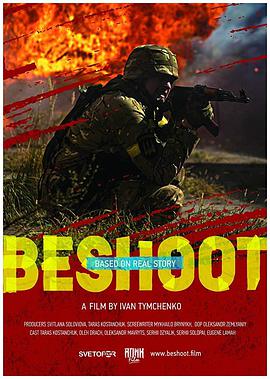剧情简介
人群熙熙攘攘,生命喧闹不已,而历史悄然无声。游客接踵摩肩,在一个个窗口探视,想象着曾经的场景。人们走过沉寂无声的监狱、曾经吊死过无数人的木桩,冷冰冰的毒气室,喝了一口水,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空旷的地方休息片刻,导游开始催促,人们满脸厌倦,还有下一个景点要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部电影很难让人心平气和的从头到尾安静看完,特别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桌子上摆着五六个不同尺寸的电子屏幕,脑子里面不断地浮现出各种凡尘杂念,闪动的充电灯,此起彼伏的手机提醒声,每一个人处于他所在的原点,好像轻而易举的拥有了无数种跟全世界联系的方式,却成就了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
《奥斯特里茨》。
IMDB上的简介如是说:欧洲还有一些地方仍然保存着历史上最痛苦的回忆——那些人类在此化成灰烬的工厂。这些地方如今是向公众开放的纪念场所,每年都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电影的标题取自于W.G. Sebald写的同名小说,致力于纪念大屠杀。这部电影是对这些纪念场所的观看者的观看,这些地方曾经是纳粹的集中营。他们为何而来?他们在寻找什么?
有人将这部电影直接视为一种对游客现象的批判,认为这是在批评将集中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的不合时宜或至少说充满争议。这样的看法,显然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想,创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将自己放在审判席上,这部电影不是一部所谓道德文章。它只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加修饰的客观呈现,而这种呈现本身不具备任何道德立场。
当我们在荧幕前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甚至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我们和他们处在相对的位置中。我们是电影的观众,是对游客及其行为的有意识的审视者。但这一点也许不难想象的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实际上都完全有可能,是出现在影片中千千万万游客中的一个。我们与游客的距离和对立,远远不及游客与历史,生者与死者的距离和对立。
从这个角度,实际上,整个世界上的人都是面对历史的游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电影里的观众,导演并不是让我们思考游客的行为,而是让我们思考自己。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将这部电影视为一种对话。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监禁与自由,死亡与生命。。。这样的二元对立也一定层面上是对于这一复杂情景的简化,却至少可以让我们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
集中营或者监狱的遗址,是历史的残存,更是野蛮行径的罪证。据介绍,影片取景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两者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称纳粹三大集中营。
我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感觉自己与那段历史的隔绝于遥远。
现实凝视着历史,人们凝视着集中营,不管是照片,书本,影片,乃至于眼前触手可及的遗址,却深深地感到与之遥不可及的距离。我们震惊于这样的事实,究竟为何在人类发展到看似高度的文明之时,竟然发生如此不可想象的惨绝人寰的屠杀。这一切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阐释,也依然是思想家哲学家思考的重大现代性症结之一。
而我们,距离这一事件真的有那么遥远吗?而我们与纳粹、与党卫军、与盖世太保、与当时心悦诚服的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国民,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汉娜阿伦特描述了这个看起来极不起眼的“纳粹魔头”,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艾希曼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行动中负责运输犹太人的总指挥之一,可是到了耶路撒冷的临时法庭,他竟然不过是一个如此孱弱、普通,顽固不化,是不是流出鼻涕的中年男人。
人们翻遍了可及的资料,想要挖掘出他身为纳粹恶魔的罪证,最后却只能找到许多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命令,事件,以及无数受害人的描述。
阿伦特最后认为,艾希曼本人(作为他自己)并不能算一个反犹分子,他以前有犹太人朋友,几乎没有任何可见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出于个人原因迫害过一个犹太人。他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执行所有上级下达的命令,调遣车队,运输一批一批的犹太人,至于运到哪里、为什么运到那里、运到那里以后犹太人将面临着什么,思考这些不是他的职责,也不是他一己之力就能改变的。也许,当时他若反抗命令,他的确可以减少犹太人的死亡数目,但是他没有反抗命令的立场,他相信并崇拜希特勒,他不过是做了当时千千万万德国人都在做的事情,按照上级的命令并一丝不苟的执行。
阿伦特解释到,这样极端的恶,竟然只不过产生于一个人放弃了身而为人的思考的能力。他放弃了思考,放弃了身为人类最基本的职责,以一种最平庸的方式,合谋制造了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惨案。阿伦特说,极恶从来都不需要是深刻的,创造这一惨案的恶,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当他来到你的面前,它是那样的平庸。相反,善良才是需要思考的,才是深刻的。
如果整个大屠杀的流程中有一百个环环相扣的环节,谁该为大屠杀负责?
当我们义正辞严,毫不犹豫的处死了命令的下达者和刽子手,那中间过程的98个环节,他们的罪责应该怎么去认定?他们应该如何平分这笼罩于人类上空永远不会散去的恶的阴霾?
而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有一个事实,有许多刽子手,也是由受害者充当的。
在电影中,一个女解说员告诉游客,有一部分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被纳粹组织成了特别工作组,他们负责管理集中营里的其他犹太人,负责组织他们的日常劳作,组织他们分组有序进入毒气室,他们打开水和煤气的开关,他们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再接着处理他们的尸体,将他们扔进焚烧炉。人们不仅看到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还要闻到焚烧尸体的臭味。
阿伦特还毫不修饰的指责二战时期和纳粹合作的犹太人委员会,尽管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也在一定情况下解救了一些犹太人,但他们造成了更巨大的恶果。犹太人委员会给自己的同胞登记造册,说服他们配合委员会和纳粹的工作,他们指挥数百万犹太人安静驯服的登上开往集中营、开往毒气室、开往永恒痛苦和黑暗的火车。没有他们,一切不可能如此井然有序,纳粹不可能奇迹般的在短短的时间里顺利的谋杀数百万犹太人。在当时内忧外困、深陷战事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让阿伦特激怒了整个犹太世界,一度让她陷入巨大的争议的漩涡之中)
然而,此刻的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立场去审判党卫军、纳粹、刽子手们?如果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立场去审判犹太人委员会?审判集中营里那些充当纳粹走狗的特别工作组?甚至于审判那些“你们为什么不反抗”的犹太人?
人群熙熙攘攘,生命喧闹不已,而历史悄然无声。游客接踵摩肩,在一个个窗口探视,想象着曾经的场景。人们走过沉寂无声的监狱、曾经吊死过无数人的木桩,冷冰冰的毒气室,喝了一口水,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空旷的地方休息片刻,导游开始催促,人们满脸厌倦,还有下一个景点要去。
我们仿佛很容易处在一种遥远的批判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和距离感让人感到安全,感到不那么沉重。而当这样一个问题出现,我们身为观看“观看”的观看者,与影片中观看集中营的观看者,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与那些被迫而后自觉成为“特别工作组”的犹太人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与那些和纳粹合作,心存一丝幻想,又或者更多是考虑自身利益的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长老有那么大的差别么?
甚至于,我们和当时德国国内的纳粹党信徒,那些相信消灭了犹太人这种人类的害虫、世界的流民就可以让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发展到更文明阶段的人,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是的,他们就是以拯救全人类的名义,杀害了数百万人类。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惨案已经发生,一切成为历史。请允许活着的人先舒一口气。
不知究竟该深感悲哀,还是应当感到庆幸。能看到一群群游客来来去去,在曾经意味着绝对的消灭的集中营参观、回顾这历史,我们内心应该或多或少本能地感到一丝欣慰。是的,他们,包括我们,都是历史的幸存者。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和平的今天,缅怀曾经死去的灵魂,思考人类曾经犯过的错,做过的恶。
但需要清醒的一点是,并非我们就是天生的审判者,而纳粹生来就是罪大恶极的罪人,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人就是不幸遭难的受害者。
其实,我们都是同一群人,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境遇下的分身和投影。我们之所以是影片的观看者,是和平时代的生存着,是平静生活的主人,并非因为我们身为自己而具有的某种特殊个人品质,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恰好生于此时此地罢了。而方才所探讨的其他的角色,同样如此。
但是,人类有可能吸取教训吗?历史还会重演吗?如果万一再度面临这样的境遇,我们如何做一个能动的人,避免重蹈覆辙?
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一具巨大机器里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或认为自己不过是在遵守命令,而将其他某些人向被害的命运推近一厘米?而心中还想着,他们离死亡还有遥不可及的一千公里,这一厘米丝毫不是造成他们被杀的原因。这不是我的责任。
而这,也许并不一定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样的遥远。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下,魔幻的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
所以尽管每一个活在此刻地球上的人,并不具备太多审判者的合法性或道德立场,但我们依然不能停止对历史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审视。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当今天的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喝着牛奶吃着面包,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坐在电脑前,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之死或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题材创作诗歌或任何文艺作品,似乎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活人的狂妄自大,是话语对沉默的利用和欺凌,具有某种野蛮的本质。
但活着的人必须将这种审视继续下去,保持清醒和冷静,审视自我和整个社会、整个所谓文明世界的运作和进程,保持思考的能力,决不放弃身而为人、身为人类思考的本能。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惨剧再次发生。
而谁都知道,即便在今天,世界上依然有许多地方,战争仍在发生。
从这个视角来看,这部电影,理所当然是批判的。
影片以人们络绎不绝的走进集中营大门开始,大门上写着,劳动创造自由。那么多活着的人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坐火车汽车源源不断地走进集中营的大门。仿佛也让我们看到当年有无数的犹太人从欧洲各地被集中起来一车一车地押送进这扇大门里来。就这同一扇大门,你仿佛可以触摸到,带着历史冰冷温度的铁门。
而影片的最后,今天的游客们带着某种疲倦、释然,若有所思或空洞目光,从这个大门旁若无人地走出来,三三两两,成群结队。而那些犹太人,同样鲜活的生命,永远的消失在扇大门的里面了。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在南京从抗日战争纪念馆走出来那一瞬间的心情。
我们是幸运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幸福的。愿我们以及后世的人们都能一直这样幸运和幸福下去,拥有自由,也拥有而且不放弃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ps
电影中一名长发男解说员的话值得思考。他说,希望就是一种生存机制。当那些犹太人心存一线希望,觉得自己会重获自由,可能还会见到自己的家人,孩子,他们选择接受现实,不去反抗党卫军,好好干好自己手里的事情。反而是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他们起来反抗了。
知乎上有一个条目,“如何理解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摘选几段回答如下:
1
阿多诺无疑被自己经历过的政治历史所摧残,他写的每个字都是这种摧残的以及间或的绝望的回响,他的批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同时他认为如果这种形式的批评活动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政治形式,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持续下去。
为此,阿多诺陷入了一个令他自己深感痛苦不安的立场。他既目睹了批评的必要,又看到了它的无效和它的较之于人民承受的苦难而显示出的优越。
一方面,艺术作品在奥斯维辛之后开始享有某种无法令人容忍的特权;另一方面,艺术必须继续下去。它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就像阿多诺和贝克特所做的,利用艺术内部的一种沉默,讲述一切的不公与苦难。——伊格尔顿 《批评家的任务》
2
但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只具有这种无关紧要的自我,那么,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趋势的作用同时也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种。日复一日的痛苦又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能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得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不再生存了,在1944年就被送进毒气炉了,他的整个存在是想象中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不正常愿望的散射物。——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