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2007 类型:生活片
主演:明星ちかげ,野中あんり
导演:石乃小生
地区:日本
语言:日语
剧情简介
妈妈取消比赛资格在小说《失踪的孩子》结尾,作者费兰特为主人公莉拉最终的消失留下一丝悬念,乔纳森·弗兰岑则感到这么写恐怕是出于费兰特并未想清楚故事到底该如何收场[1]。老年的莉拉抛下了所有人,抛下她深爱的、曾寄予厚望的儿子里诺。当我第一眼看到《我母亲的消失》的海报和简介时,立刻觉得自己找到了莉拉和里诺的现实版本:想要消失的母亲贝内黛塔和想要挽留的儿子本,对应着小说中坚决的母亲和茫然的儿子——这个念头完完全全诱惑了我去看这部纪录片,期待或许在现实的层面上的「结局」能填补我们对小说悬念的执着。母子战争「不知为何,我从小到大都在拍摄我的母亲。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爱的一个模特。当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决定要离开而且再也不回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做好让她走的准备。」——随着片头字幕卡的独白,儿子、亦是本片导演的贝尼安米(昵称「本」)陈述自己在即将失去母亲的焦虑中开始了创作:他决定用影像留住母亲,深入母亲关于「消失」的想法。摄影机镜头跟随着他的母亲,这位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享有声誉的时尚模特在今天仍然活跃:领奖、授课、工作,或许作为最合适的拍摄者,导演将那些台前的和幕后的、公开的和私密的影像尽收其中,还有本以前拍摄的许多家庭私影像。此外,影片中包含一个更有野心的艺术计划:再创作母亲当年被拍下的知名写真——在复刻的影像中发掘母亲的身影,「收集并存下她留下的财富」[2]。所以,它也像一部人物专题纪录片那样组织起种种文献——照片、影像资料、文字叙述和私人录影,来谱写母亲的人生历程。但作为儿子,导演首先遭遇了困难,这也是反映在家庭纪录影像制作中代际间常见的困难:家长拒绝配合。在影片《35号公墓》(2017)中,当法国演员兼导演埃里克·卡拉瓦卡开始探寻家庭秘史时,发生了一桩「罗生门」事件:他母亲和父亲对早逝的女儿的陈述并不一致,一个说孩子活到3岁,另一个说她在4个月大的时候夭折。那么谁在说谎?为什么?抑或有人说了真话吗?卡拉瓦卡几乎无从在父母口中得知更多。比起谎言和拒认,《日常对话》(2016)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沉默。「为什么你都不告诉们关于你的事?」「你都不想知道吗?我告诉好不好?」当导演黄惠侦几次向母亲发问,母亲很少回应,她在镜头面前和女儿长久地僵持着。甚至在纪录短片《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2016)中,摄影机虽然成功地捕捉了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影像,但这被捕捉的「表象」恰恰成了问题:爸爸和妈妈是真心实意想出远门看海吗?他们有在摄影机面前强颜欢笑吗?孩子手中的摄影机或许让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可见,甚至作为对家长式权威的一种挑战,但真的要左右拍摄者的意志又谈何容易。贝内黛塔的不合作则更加彻底,她直接反对儿子的工作方式。在一次起床后、在友人来访时,她都打断了儿子的拍摄,甚至当摄影机让她感到烦躁时,她愤怒地让儿子滚开。作为常年被拍摄而成名的贝内黛塔,一直在反思被摄和被凝视的问题,因此她非常明确地质疑本的拍摄行为:镜头可不是你自身,镜头是敌人。另一方面,本并没有停止拍摄,从影片中穿插的导演年轻时的自拍和家庭录像中可以看出,他从孩童起就把摄影机当玩具,愉快地探索着影像的游戏。这既是导演的独白:用摄影机拍下对象、用影像纪录珍爱的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习和就业,从学校毕业后贝尼安米·巴雷斯成为职业摄影师及导演。这孑然对立的立场反映在影片之中,恰如一则简介所描述的那样:是母与子之间的拉锯战。谎言/游戏对于贝内黛塔·巴兹尼这样的影片主人公,我们似乎总有许多好说。60年代,20岁的贝内黛塔成为时装模特,随后被《Vouge》杂志最著名的编辑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相中邀请到纽约工作。贝内黛塔成为登上美国版《Vouge》封面的第一位意大利籍模特,与欧文·佩恩(Irving Penn)、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乌戈·穆拉斯(Ugo Mulas)等知名摄影师合作。1966年,登上《时尚芭莎》「全球百大美人」榜单的贝内黛塔正逢模特事业的巅峰,她常常出入安迪·沃霍尔的「工厂」,还结识了达利、杜尚等艺术家,沃霍尔的合作者杰拉德·马加拉(Gerard Malanga)为她写下很多诗句。1968年她回到意大利想往演艺圈发展,之后结婚生子。[3] 对大多数时装模特而言,他们职业生涯非常短暂——在今天也是如此,平均为5年。而贝内黛塔这样的顶级模特,在1973年退出了模特圈子,在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大潮中,她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与左翼抵抗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存留下母亲的事迹,影片中逐一回顾了上述这段历程,从众多艺文界人士的「缪斯」,到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活动家,以及从10多年前开始她进入大学授课,她讲授的课题包括「时尚与人类学」、「艺术与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2016年,贝内黛塔准备从教学岗位上退休,这是《我母亲的消失》拍摄的起点——纪录作为老师的母亲和她的学生们,这也获得了贝内黛塔同意,整个拍摄历时3年。[4] 有意思的是,在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贝内黛塔并没有告诉这个小儿子她曾经是知名的模特,反倒是本小时候自己在母亲上锁的大橱柜里找到了她的照片。[5] 母子之间好像从一开始就在捉迷藏,在影片中也是这样。本经常玩闹似地挑衅母亲:他偷拍,指摘妈妈不洗头,还挑剔她的行头,连领奖这种公共场合也不换身好看的衣服。通过其他模特对母亲以前的写真进行「再创作」未尝不是本的游戏之一,他在这些身影里寻找母亲的踪迹。而在影片进入尾声时,当母亲穿着蓝色裙子旋转,摆着当年标志性的pose,就像是游戏的完美终局,她终于重合了儿子心中模特母亲的形象。在儿子的游戏中贝内黛塔时而回应,摆起她的pose,时而进行互相伤害,鄙视他的拍摄——这就好像是他们的沟通方式之一。对于贝内黛塔而言这很明确,作为模特的走秀和拍摄是养家糊口用的,做模特和被观看就是一场大型的游戏。比较特殊的是,与此同时贝内黛塔又坚决反对着随大众图像传媒和消费社会而兴起的视觉中心主义文化(——往往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凝视),这就将她拉入了更为深层的悖谬或游戏之中。在这样的主导文化中,被摄者(subject)亦被称作「主体」,但他们真的有被认真对待吗?在《美丽的标价》一书中,阿什利·米尔斯就以「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探究了时尚模特的劳动在文化生产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总体上模特们都以「外形」作为交换的资本,但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致的是,和外表更符合主流审美、多参与大众市场产品目录或平面广告拍摄的商业模特相比,外形特别、参与时装走秀和大牌拍摄的文艺模特,无论在薪资水平、稳定性上都远低于前者。后者往往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资本进行赌博,以争取那捉摸不定却又更有价值的「艺术性」声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能从中脱颖而出、扬名立万。[6] 在「高概念」这类美好词汇的包装下,从事文艺拍摄的模特还受到了另类的剥削:他们很多时候连钱都拿不到,取而代之的「我为《XXX》拍过大片」的声誉,或者一些设计师单品,甚至只是精品店的优惠券。在影视行业中,主打明星同样也会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明星制毋宁说是可怕的,签署姓名无非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和利润,为了维持这种效应,制片厂严苛地掌控着明星的「人设」。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没有剥削的电影[7],今天演员的权益在很大意义上得到改善,甚至「有个性」也转化为一种可流通的资本。但在具体的视角下,被拍摄者的主体性仍然是个大问题,比如在性别视角下,女性演员往往是被物化的和沉默的。在70年代,法国演员德菲因·塞里格和导演卡罗尔·罗索普洛斯就尝试打破女演员长久的沉默,她们采访美国和法国女演员制成影片《美丽噤声》(1981)。当被问及「如果你是男人你还会当演员吗」、「你喜欢你演的角色吗」等问题时,受访者们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卡罗尔和德菲因选择了接近古板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对话,即始终采用固定镜头拍摄,这意味着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和倾听。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在《美丽噤声》中说她遇到的导演们总是告诉她「这个角色的为你量身定做,这就是你」,然而当她观看自己主演的《中国姑娘》(1967)时却觉得那根本不是她自己。对贝内黛塔而言这个问题是一致的:照片中的她是真的她吗?尽管艺术家和她有时都在作品上留下签名,但那个她是真的她吗?我们翻来覆去地把某人介绍为「某某人的缪斯」,这种说法未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亦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更何况在大众文化中、在艺术品市场中,我们对杜尚、达利、沃霍尔等人的追捧和关注,不是要比对他们「缪斯」的关注要多得多吗。正是通过揭示影像作品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品,才让人意识到图像是如何被征用的这一问题,这也正是贝内黛塔反对影像的论据。不可能性当然,导演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涉及更多,其实在母亲的课堂上,以及母亲和学生的接触中,还有导演和参与「复刻计划」的模特的交流中,是有机会听见更多声音的。或许不该这么苛求一部影片,毕竟无论是在影片摄制过程中,还是在此后面对观众的回应中,作为影像工作者的导演都宣称逐渐理解了母亲提出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影片中,本多次向母亲询问「消失」的具体含义或计划,作为儿子他最希望理解的恐怕还是母亲的这个「怪念头」。当她对儿子说出「我更感兴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而不是可见的」,「比起显现,我更想要消隐」,此时母亲的形象变得陌异起来。回到家庭影像,我始终逃不过这一追问: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我们彼此说话,但真的理解对方吗?两代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基于这沟通的不可能性,许多创作者开发出不同的影像策略。在《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中,导演王坪和同伴兼摄影师沈蕊兰之间的一段对话替代了一家人游玩影像的声轨,那是她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到和想到的。对父母而言,不曾见过的大海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又为何总是提起死亡?在这些通过沟通无法穿透的疑问中,和伙伴的对话和反思让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状态变得更为立体和复杂。《35号公墓》的导演面对不再透露更多的父母,选择剑走偏锋:述诸历史的宏大叙事,他把家庭故事汇合进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背景,在其中侦探早逝姐姐身世、乃至整个家族的蛛丝马迹。在《日常对话》中,面对家族长辈对母亲秘密的三缄其口,黄惠侦直接向他们发起进攻,她追问:既然你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怎么这么冷静」?此时的镜头凝滞,所有的表情、眼神、小动作都在里面。面对不愿谈论自己「不是秘密的秘密」的母亲,黄也不依不饶,前一秒仍拒绝沟通的母亲,后一秒都被自己「带女生回家却不愿谈论」的悖谬惹笑了。通过不断展现过往的DV,展现女朋友们和亲人不断地谈论,以及他们面对禁忌的不同态度,她鼓起勇气揭开自己秘密和创伤,而所有这些难道不也是为了让母亲和观众直面伤痛所作的准备吗。沟通之不可能在这些影像中最终都没有被消解,相反,纪录片作者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将冲突转为张力。正是在个意义上,私密性的影像有了普遍性的联结点,对观众而言,情感的冲击和扰动不仅仅指向了他自身的处境和记忆,也打开了公共性的维度: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究竟如何相处。《我母亲的消失》中「战争」和游戏诚然呈现了母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影像策略的思考上贝尼安米有着自己的一贯性:无论是作为儿子观察母亲,还是客观地观察模特、教育者贝内黛塔,基本上他采取了贝内黛塔所反对的将被摄者牢牢固定在图像之中的方式。影片皆大欢喜的结尾也是如此,十分讨巧安排由母亲「掌控」一次摄影机,似乎让这个影像游戏更具辩证意味。实际上,结尾虚拟了母亲在海面上漂流,并准备驶向某个无人之处,无非是再次将母亲「消失」这一行为收入自己的「玩具收藏盒」中。导演当真如他所言的理解了母亲吗?这难道没有表现出一种对情感羁绊、亲密关系的错误理解和幼稚态度:它们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解和认同之上,而只有如此我们才有话可说。根本没有这种必要,需要的只有倾听。贝内黛塔在几处访谈中都明确表示,她既不曾享受过60年代任何一次拍摄,也不曾喜欢纽约这座城市,即便受到过肯尼迪家族这样的名门邀请,在聚会上她也只不过是像洋娃娃一样的玩弄对象,这一切都不好受。[8] 她是否认为将来会有更道德的时尚产业出现?「不会。或许再过两百年。」——这是原话[9]。 对于《我母亲的消失》更实际的不满和担忧是,事实上,有更多人(比如女权主义者)会和贝内黛塔产生并不存在沟通的联结或共通,从一些观众对影片的评论中显然已经能够看出这点。在荧幕之外,人们比导演更多地体会到了贝内黛塔所期望的「消失/消隐」的涵义,正如我们知道莉拉从未消失一样,她只是走进黑夜之中。就像《失踪的孩子》中的最后一行——莱农想着:「现在莉拉那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我应该放弃继续找她。」[1] 参见纪录片《费兰特热潮》(Ferrante Fever,2017)中对弗兰岑的访谈。[2] 参见《我母亲的消失》官方网站(https://www.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com/)的导演手记。[3] 参见“The Boldly Heroic Benedetta Barzini: Marxist, Model and Muse”,作者Sophie Bew。https://www.anothermag.com/fashion-beauty/10099/the-boldly-heroic-benedetta-barzini-marxist-model-and-muse[4] 参见导演访谈“The Camera Is Evil in Sundance’s ‘The Disappearance of My Mother’”。https://nofilmschool.com/2020/01/disappearance-my-mother-sundance[5] 参见官方网站导演手记。[6] 参见《美丽的标价》“第二章 T台经济学”,阿什利·米尔斯著,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引自《美国独立电影》,约翰·贝拉主编,朱鸿飞、萧达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参见“Benedetta Barzini On The Art Of Ageing Gracefully”,https://www.vogue.co.uk/article/benedetta-barzini-on-ageing,以及访谈“New York’s unreciprocated love for Benedetta Barzini”,https://www.documentjournal.com/2018/10/new-yorks-unreciprocated-love-for-benedetta-barzini/。[9] 参见贝内黛塔和《Interview》杂志的访谈:“The Disappearing Act of Benedetta Barzini”,采访人:Conor Williams,https://www.interviewmagazine.com/film/benedetta-barzini-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beniamino-barrese。——原载于「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公众号」——
{if:"在小说《失踪的孩子》结尾,作者费兰特为主人公莉拉最终的消失留下一丝悬念,乔纳森·弗兰岑则感到这么写恐怕是出于费兰特并未想清楚故事到底该如何收场[1]。老年的莉拉抛下了所有人,抛下她深爱的、曾寄予厚望的儿子里诺。当我第一眼看到《我母亲的消失》的海报和简介时,立刻觉得自己找到了莉拉和里诺的现实版本:想要消失的母亲贝内黛塔和想要挽留的儿子本,对应着小说中坚决的母亲和茫然的儿子——这个念头完完全全诱惑了我去看这部纪录片,期待或许在现实的层面上的「结局」能填补我们对小说悬念的执着。母子战争「不知为何,我从小到大都在拍摄我的母亲。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爱的一个模特。当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决定要离开而且再也不回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做好让她走的准备。」——随着片头字幕卡的独白,儿子、亦是本片导演的贝尼安米(昵称「本」)陈述自己在即将失去母亲的焦虑中开始了创作:他决定用影像留住母亲,深入母亲关于「消失」的想法。摄影机镜头跟随着他的母亲,这位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享有声誉的时尚模特在今天仍然活跃:领奖、授课、工作,或许作为最合适的拍摄者,导演将那些台前的和幕后的、公开的和私密的影像尽收其中,还有本以前拍摄的许多家庭私影像。此外,影片中包含一个更有野心的艺术计划:再创作母亲当年被拍下的知名写真——在复刻的影像中发掘母亲的身影,「收集并存下她留下的财富」[2]。所以,它也像一部人物专题纪录片那样组织起种种文献——照片、影像资料、文字叙述和私人录影,来谱写母亲的人生历程。但作为儿子,导演首先遭遇了困难,这也是反映在家庭纪录影像制作中代际间常见的困难:家长拒绝配合。在影片《35号公墓》(2017)中,当法国演员兼导演埃里克·卡拉瓦卡开始探寻家庭秘史时,发生了一桩「罗生门」事件:他母亲和父亲对早逝的女儿的陈述并不一致,一个说孩子活到3岁,另一个说她在4个月大的时候夭折。那么谁在说谎?为什么?抑或有人说了真话吗?卡拉瓦卡几乎无从在父母口中得知更多。比起谎言和拒认,《日常对话》(2016)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沉默。「为什么你都不告诉们关于你的事?」「你都不想知道吗?我告诉好不好?」当导演黄惠侦几次向母亲发问,母亲很少回应,她在镜头面前和女儿长久地僵持着。甚至在纪录短片《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2016)中,摄影机虽然成功地捕捉了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影像,但这被捕捉的「表象」恰恰成了问题:爸爸和妈妈是真心实意想出远门看海吗?他们有在摄影机面前强颜欢笑吗?孩子手中的摄影机或许让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可见,甚至作为对家长式权威的一种挑战,但真的要左右拍摄者的意志又谈何容易。贝内黛塔的不合作则更加彻底,她直接反对儿子的工作方式。在一次起床后、在友人来访时,她都打断了儿子的拍摄,甚至当摄影机让她感到烦躁时,她愤怒地让儿子滚开。作为常年被拍摄而成名的贝内黛塔,一直在反思被摄和被凝视的问题,因此她非常明确地质疑本的拍摄行为:镜头可不是你自身,镜头是敌人。另一方面,本并没有停止拍摄,从影片中穿插的导演年轻时的自拍和家庭录像中可以看出,他从孩童起就把摄影机当玩具,愉快地探索着影像的游戏。这既是导演的独白:用摄影机拍下对象、用影像纪录珍爱的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习和就业,从学校毕业后贝尼安米·巴雷斯成为职业摄影师及导演。这孑然对立的立场反映在影片之中,恰如一则简介所描述的那样:是母与子之间的拉锯战。谎言/游戏对于贝内黛塔·巴兹尼这样的影片主人公,我们似乎总有许多好说。60年代,20岁的贝内黛塔成为时装模特,随后被《Vouge》杂志最著名的编辑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相中邀请到纽约工作。贝内黛塔成为登上美国版《Vouge》封面的第一位意大利籍模特,与欧文·佩恩(Irving Penn)、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乌戈·穆拉斯(Ugo Mulas)等知名摄影师合作。1966年,登上《时尚芭莎》「全球百大美人」榜单的贝内黛塔正逢模特事业的巅峰,她常常出入安迪·沃霍尔的「工厂」,还结识了达利、杜尚等艺术家,沃霍尔的合作者杰拉德·马加拉(Gerard Malanga)为她写下很多诗句。1968年她回到意大利想往演艺圈发展,之后结婚生子。[3] 对大多数时装模特而言,他们职业生涯非常短暂——在今天也是如此,平均为5年。而贝内黛塔这样的顶级模特,在1973年退出了模特圈子,在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大潮中,她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与左翼抵抗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存留下母亲的事迹,影片中逐一回顾了上述这段历程,从众多艺文界人士的「缪斯」,到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活动家,以及从10多年前开始她进入大学授课,她讲授的课题包括「时尚与人类学」、「艺术与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2016年,贝内黛塔准备从教学岗位上退休,这是《我母亲的消失》拍摄的起点——纪录作为老师的母亲和她的学生们,这也获得了贝内黛塔同意,整个拍摄历时3年。[4] 有意思的是,在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贝内黛塔并没有告诉这个小儿子她曾经是知名的模特,反倒是本小时候自己在母亲上锁的大橱柜里找到了她的照片。[5] 母子之间好像从一开始就在捉迷藏,在影片中也是这样。本经常玩闹似地挑衅母亲:他偷拍,指摘妈妈不洗头,还挑剔她的行头,连领奖这种公共场合也不换身好看的衣服。通过其他模特对母亲以前的写真进行「再创作」未尝不是本的游戏之一,他在这些身影里寻找母亲的踪迹。而在影片进入尾声时,当母亲穿着蓝色裙子旋转,摆着当年标志性的pose,就像是游戏的完美终局,她终于重合了儿子心中模特母亲的形象。在儿子的游戏中贝内黛塔时而回应,摆起她的pose,时而进行互相伤害,鄙视他的拍摄——这就好像是他们的沟通方式之一。对于贝内黛塔而言这很明确,作为模特的走秀和拍摄是养家糊口用的,做模特和被观看就是一场大型的游戏。比较特殊的是,与此同时贝内黛塔又坚决反对着随大众图像传媒和消费社会而兴起的视觉中心主义文化(——往往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凝视),这就将她拉入了更为深层的悖谬或游戏之中。在这样的主导文化中,被摄者(subject)亦被称作「主体」,但他们真的有被认真对待吗?在《美丽的标价》一书中,阿什利·米尔斯就以「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探究了时尚模特的劳动在文化生产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总体上模特们都以「外形」作为交换的资本,但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致的是,和外表更符合主流审美、多参与大众市场产品目录或平面广告拍摄的商业模特相比,外形特别、参与时装走秀和大牌拍摄的文艺模特,无论在薪资水平、稳定性上都远低于前者。后者往往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资本进行赌博,以争取那捉摸不定却又更有价值的「艺术性」声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能从中脱颖而出、扬名立万。[6] 在「高概念」这类美好词汇的包装下,从事文艺拍摄的模特还受到了另类的剥削:他们很多时候连钱都拿不到,取而代之的「我为《XXX》拍过大片」的声誉,或者一些设计师单品,甚至只是精品店的优惠券。在影视行业中,主打明星同样也会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明星制毋宁说是可怕的,签署姓名无非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和利润,为了维持这种效应,制片厂严苛地掌控着明星的「人设」。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没有剥削的电影[7],今天演员的权益在很大意义上得到改善,甚至「有个性」也转化为一种可流通的资本。但在具体的视角下,被拍摄者的主体性仍然是个大问题,比如在性别视角下,女性演员往往是被物化的和沉默的。在70年代,法国演员德菲因·塞里格和导演卡罗尔·罗索普洛斯就尝试打破女演员长久的沉默,她们采访美国和法国女演员制成影片《美丽噤声》(1981)。当被问及「如果你是男人你还会当演员吗」、「你喜欢你演的角色吗」等问题时,受访者们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卡罗尔和德菲因选择了接近古板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对话,即始终采用固定镜头拍摄,这意味着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和倾听。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在《美丽噤声》中说她遇到的导演们总是告诉她「这个角色的为你量身定做,这就是你」,然而当她观看自己主演的《中国姑娘》(1967)时却觉得那根本不是她自己。对贝内黛塔而言这个问题是一致的:照片中的她是真的她吗?尽管艺术家和她有时都在作品上留下签名,但那个她是真的她吗?我们翻来覆去地把某人介绍为「某某人的缪斯」,这种说法未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亦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更何况在大众文化中、在艺术品市场中,我们对杜尚、达利、沃霍尔等人的追捧和关注,不是要比对他们「缪斯」的关注要多得多吗。正是通过揭示影像作品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品,才让人意识到图像是如何被征用的这一问题,这也正是贝内黛塔反对影像的论据。不可能性当然,导演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涉及更多,其实在母亲的课堂上,以及母亲和学生的接触中,还有导演和参与「复刻计划」的模特的交流中,是有机会听见更多声音的。或许不该这么苛求一部影片,毕竟无论是在影片摄制过程中,还是在此后面对观众的回应中,作为影像工作者的导演都宣称逐渐理解了母亲提出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影片中,本多次向母亲询问「消失」的具体含义或计划,作为儿子他最希望理解的恐怕还是母亲的这个「怪念头」。当她对儿子说出「我更感兴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而不是可见的」,「比起显现,我更想要消隐」,此时母亲的形象变得陌异起来。回到家庭影像,我始终逃不过这一追问: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我们彼此说话,但真的理解对方吗?两代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基于这沟通的不可能性,许多创作者开发出不同的影像策略。在《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中,导演王坪和同伴兼摄影师沈蕊兰之间的一段对话替代了一家人游玩影像的声轨,那是她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到和想到的。对父母而言,不曾见过的大海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又为何总是提起死亡?在这些通过沟通无法穿透的疑问中,和伙伴的对话和反思让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状态变得更为立体和复杂。《35号公墓》的导演面对不再透露更多的父母,选择剑走偏锋:述诸历史的宏大叙事,他把家庭故事汇合进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背景,在其中侦探早逝姐姐身世、乃至整个家族的蛛丝马迹。在《日常对话》中,面对家族长辈对母亲秘密的三缄其口,黄惠侦直接向他们发起进攻,她追问:既然你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怎么这么冷静」?此时的镜头凝滞,所有的表情、眼神、小动作都在里面。面对不愿谈论自己「不是秘密的秘密」的母亲,黄也不依不饶,前一秒仍拒绝沟通的母亲,后一秒都被自己「带女生回家却不愿谈论」的悖谬惹笑了。通过不断展现过往的DV,展现女朋友们和亲人不断地谈论,以及他们面对禁忌的不同态度,她鼓起勇气揭开自己秘密和创伤,而所有这些难道不也是为了让母亲和观众直面伤痛所作的准备吗。沟通之不可能在这些影像中最终都没有被消解,相反,纪录片作者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将冲突转为张力。正是在个意义上,私密性的影像有了普遍性的联结点,对观众而言,情感的冲击和扰动不仅仅指向了他自身的处境和记忆,也打开了公共性的维度: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究竟如何相处。《我母亲的消失》中「战争」和游戏诚然呈现了母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影像策略的思考上贝尼安米有着自己的一贯性:无论是作为儿子观察母亲,还是客观地观察模特、教育者贝内黛塔,基本上他采取了贝内黛塔所反对的将被摄者牢牢固定在图像之中的方式。影片皆大欢喜的结尾也是如此,十分讨巧安排由母亲「掌控」一次摄影机,似乎让这个影像游戏更具辩证意味。实际上,结尾虚拟了母亲在海面上漂流,并准备驶向某个无人之处,无非是再次将母亲「消失」这一行为收入自己的「玩具收藏盒」中。导演当真如他所言的理解了母亲吗?这难道没有表现出一种对情感羁绊、亲密关系的错误理解和幼稚态度:它们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解和认同之上,而只有如此我们才有话可说。根本没有这种必要,需要的只有倾听。贝内黛塔在几处访谈中都明确表示,她既不曾享受过60年代任何一次拍摄,也不曾喜欢纽约这座城市,即便受到过肯尼迪家族这样的名门邀请,在聚会上她也只不过是像洋娃娃一样的玩弄对象,这一切都不好受。[8] 她是否认为将来会有更道德的时尚产业出现?「不会。或许再过两百年。」——这是原话[9]。 对于《我母亲的消失》更实际的不满和担忧是,事实上,有更多人(比如女权主义者)会和贝内黛塔产生并不存在沟通的联结或共通,从一些观众对影片的评论中显然已经能够看出这点。在荧幕之外,人们比导演更多地体会到了贝内黛塔所期望的「消失/消隐」的涵义,正如我们知道莉拉从未消失一样,她只是走进黑夜之中。就像《失踪的孩子》中的最后一行——莱农想着:「现在莉拉那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我应该放弃继续找她。」[1] 参见纪录片《费兰特热潮》(Ferrante Fever,2017)中对弗兰岑的访谈。[2] 参见《我母亲的消失》官方网站(https://www.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com/)的导演手记。[3] 参见“The Boldly Heroic Benedetta Barzini: Marxist, Model and Muse”,作者Sophie Bew。https://www.anothermag.com/fashion-beauty/10099/the-boldly-heroic-benedetta-barzini-marxist-model-and-muse[4] 参见导演访谈“The Camera Is Evil in Sundance’s ‘The Disappearance of My Mother’”。https://nofilmschool.com/2020/01/disappearance-my-mother-sundance[5] 参见官方网站导演手记。[6] 参见《美丽的标价》“第二章 T台经济学”,阿什利·米尔斯著,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引自《美国独立电影》,约翰·贝拉主编,朱鸿飞、萧达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参见“Benedetta Barzini On The Art Of Ageing Gracefully”,https://www.vogue.co.uk/article/benedetta-barzini-on-ageing,以及访谈“New York’s unreciprocated love for Benedetta Barzini”,https://www.documentjournal.com/2018/10/new-yorks-unreciprocated-love-for-benedetta-barzini/。[9] 参见贝内黛塔和《Interview》杂志的访谈:“The Disappearing Act of Benedetta Barzini”,采访人:Conor Williams,https://www.interviewmagazine.com/film/benedetta-barzini-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beniamino-barrese。——原载于「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公众号」——"<>"" && "在小说《失踪的孩子》结尾,作者费兰特为主人公莉拉最终的消失留下一丝悬念,乔纳森·弗兰岑则感到这么写恐怕是出于费兰特并未想清楚故事到底该如何收场[1]。老年的莉拉抛下了所有人,抛下她深爱的、曾寄予厚望的儿子里诺。当我第一眼看到《我母亲的消失》的海报和简介时,立刻觉得自己找到了莉拉和里诺的现实版本:想要消失的母亲贝内黛塔和想要挽留的儿子本,对应着小说中坚决的母亲和茫然的儿子——这个念头完完全全诱惑了我去看这部纪录片,期待或许在现实的层面上的「结局」能填补我们对小说悬念的执着。母子战争「不知为何,我从小到大都在拍摄我的母亲。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爱的一个模特。当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决定要离开而且再也不回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做好让她走的准备。」——随着片头字幕卡的独白,儿子、亦是本片导演的贝尼安米(昵称「本」)陈述自己在即将失去母亲的焦虑中开始了创作:他决定用影像留住母亲,深入母亲关于「消失」的想法。摄影机镜头跟随着他的母亲,这位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享有声誉的时尚模特在今天仍然活跃:领奖、授课、工作,或许作为最合适的拍摄者,导演将那些台前的和幕后的、公开的和私密的影像尽收其中,还有本以前拍摄的许多家庭私影像。此外,影片中包含一个更有野心的艺术计划:再创作母亲当年被拍下的知名写真——在复刻的影像中发掘母亲的身影,「收集并存下她留下的财富」[2]。所以,它也像一部人物专题纪录片那样组织起种种文献——照片、影像资料、文字叙述和私人录影,来谱写母亲的人生历程。但作为儿子,导演首先遭遇了困难,这也是反映在家庭纪录影像制作中代际间常见的困难:家长拒绝配合。在影片《35号公墓》(2017)中,当法国演员兼导演埃里克·卡拉瓦卡开始探寻家庭秘史时,发生了一桩「罗生门」事件:他母亲和父亲对早逝的女儿的陈述并不一致,一个说孩子活到3岁,另一个说她在4个月大的时候夭折。那么谁在说谎?为什么?抑或有人说了真话吗?卡拉瓦卡几乎无从在父母口中得知更多。比起谎言和拒认,《日常对话》(2016)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沉默。「为什么你都不告诉们关于你的事?」「你都不想知道吗?我告诉好不好?」当导演黄惠侦几次向母亲发问,母亲很少回应,她在镜头面前和女儿长久地僵持着。甚至在纪录短片《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2016)中,摄影机虽然成功地捕捉了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影像,但这被捕捉的「表象」恰恰成了问题:爸爸和妈妈是真心实意想出远门看海吗?他们有在摄影机面前强颜欢笑吗?孩子手中的摄影机或许让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可见,甚至作为对家长式权威的一种挑战,但真的要左右拍摄者的意志又谈何容易。贝内黛塔的不合作则更加彻底,她直接反对儿子的工作方式。在一次起床后、在友人来访时,她都打断了儿子的拍摄,甚至当摄影机让她感到烦躁时,她愤怒地让儿子滚开。作为常年被拍摄而成名的贝内黛塔,一直在反思被摄和被凝视的问题,因此她非常明确地质疑本的拍摄行为:镜头可不是你自身,镜头是敌人。另一方面,本并没有停止拍摄,从影片中穿插的导演年轻时的自拍和家庭录像中可以看出,他从孩童起就把摄影机当玩具,愉快地探索着影像的游戏。这既是导演的独白:用摄影机拍下对象、用影像纪录珍爱的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习和就业,从学校毕业后贝尼安米·巴雷斯成为职业摄影师及导演。这孑然对立的立场反映在影片之中,恰如一则简介所描述的那样:是母与子之间的拉锯战。谎言/游戏对于贝内黛塔·巴兹尼这样的影片主人公,我们似乎总有许多好说。60年代,20岁的贝内黛塔成为时装模特,随后被《Vouge》杂志最著名的编辑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相中邀请到纽约工作。贝内黛塔成为登上美国版《Vouge》封面的第一位意大利籍模特,与欧文·佩恩(Irving Penn)、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乌戈·穆拉斯(Ugo Mulas)等知名摄影师合作。1966年,登上《时尚芭莎》「全球百大美人」榜单的贝内黛塔正逢模特事业的巅峰,她常常出入安迪·沃霍尔的「工厂」,还结识了达利、杜尚等艺术家,沃霍尔的合作者杰拉德·马加拉(Gerard Malanga)为她写下很多诗句。1968年她回到意大利想往演艺圈发展,之后结婚生子。[3] 对大多数时装模特而言,他们职业生涯非常短暂——在今天也是如此,平均为5年。而贝内黛塔这样的顶级模特,在1973年退出了模特圈子,在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大潮中,她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与左翼抵抗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存留下母亲的事迹,影片中逐一回顾了上述这段历程,从众多艺文界人士的「缪斯」,到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活动家,以及从10多年前开始她进入大学授课,她讲授的课题包括「时尚与人类学」、「艺术与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2016年,贝内黛塔准备从教学岗位上退休,这是《我母亲的消失》拍摄的起点——纪录作为老师的母亲和她的学生们,这也获得了贝内黛塔同意,整个拍摄历时3年。[4] 有意思的是,在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贝内黛塔并没有告诉这个小儿子她曾经是知名的模特,反倒是本小时候自己在母亲上锁的大橱柜里找到了她的照片。[5] 母子之间好像从一开始就在捉迷藏,在影片中也是这样。本经常玩闹似地挑衅母亲:他偷拍,指摘妈妈不洗头,还挑剔她的行头,连领奖这种公共场合也不换身好看的衣服。通过其他模特对母亲以前的写真进行「再创作」未尝不是本的游戏之一,他在这些身影里寻找母亲的踪迹。而在影片进入尾声时,当母亲穿着蓝色裙子旋转,摆着当年标志性的pose,就像是游戏的完美终局,她终于重合了儿子心中模特母亲的形象。在儿子的游戏中贝内黛塔时而回应,摆起她的pose,时而进行互相伤害,鄙视他的拍摄——这就好像是他们的沟通方式之一。对于贝内黛塔而言这很明确,作为模特的走秀和拍摄是养家糊口用的,做模特和被观看就是一场大型的游戏。比较特殊的是,与此同时贝内黛塔又坚决反对着随大众图像传媒和消费社会而兴起的视觉中心主义文化(——往往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凝视),这就将她拉入了更为深层的悖谬或游戏之中。在这样的主导文化中,被摄者(subject)亦被称作「主体」,但他们真的有被认真对待吗?在《美丽的标价》一书中,阿什利·米尔斯就以「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探究了时尚模特的劳动在文化生产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总体上模特们都以「外形」作为交换的资本,但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致的是,和外表更符合主流审美、多参与大众市场产品目录或平面广告拍摄的商业模特相比,外形特别、参与时装走秀和大牌拍摄的文艺模特,无论在薪资水平、稳定性上都远低于前者。后者往往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资本进行赌博,以争取那捉摸不定却又更有价值的「艺术性」声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能从中脱颖而出、扬名立万。[6] 在「高概念」这类美好词汇的包装下,从事文艺拍摄的模特还受到了另类的剥削:他们很多时候连钱都拿不到,取而代之的「我为《XXX》拍过大片」的声誉,或者一些设计师单品,甚至只是精品店的优惠券。在影视行业中,主打明星同样也会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明星制毋宁说是可怕的,签署姓名无非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和利润,为了维持这种效应,制片厂严苛地掌控着明星的「人设」。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没有剥削的电影[7],今天演员的权益在很大意义上得到改善,甚至「有个性」也转化为一种可流通的资本。但在具体的视角下,被拍摄者的主体性仍然是个大问题,比如在性别视角下,女性演员往往是被物化的和沉默的。在70年代,法国演员德菲因·塞里格和导演卡罗尔·罗索普洛斯就尝试打破女演员长久的沉默,她们采访美国和法国女演员制成影片《美丽噤声》(1981)。当被问及「如果你是男人你还会当演员吗」、「你喜欢你演的角色吗」等问题时,受访者们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卡罗尔和德菲因选择了接近古板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对话,即始终采用固定镜头拍摄,这意味着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和倾听。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在《美丽噤声》中说她遇到的导演们总是告诉她「这个角色的为你量身定做,这就是你」,然而当她观看自己主演的《中国姑娘》(1967)时却觉得那根本不是她自己。对贝内黛塔而言这个问题是一致的:照片中的她是真的她吗?尽管艺术家和她有时都在作品上留下签名,但那个她是真的她吗?我们翻来覆去地把某人介绍为「某某人的缪斯」,这种说法未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亦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更何况在大众文化中、在艺术品市场中,我们对杜尚、达利、沃霍尔等人的追捧和关注,不是要比对他们「缪斯」的关注要多得多吗。正是通过揭示影像作品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品,才让人意识到图像是如何被征用的这一问题,这也正是贝内黛塔反对影像的论据。不可能性当然,导演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涉及更多,其实在母亲的课堂上,以及母亲和学生的接触中,还有导演和参与「复刻计划」的模特的交流中,是有机会听见更多声音的。或许不该这么苛求一部影片,毕竟无论是在影片摄制过程中,还是在此后面对观众的回应中,作为影像工作者的导演都宣称逐渐理解了母亲提出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影片中,本多次向母亲询问「消失」的具体含义或计划,作为儿子他最希望理解的恐怕还是母亲的这个「怪念头」。当她对儿子说出「我更感兴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而不是可见的」,「比起显现,我更想要消隐」,此时母亲的形象变得陌异起来。回到家庭影像,我始终逃不过这一追问: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我们彼此说话,但真的理解对方吗?两代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基于这沟通的不可能性,许多创作者开发出不同的影像策略。在《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中,导演王坪和同伴兼摄影师沈蕊兰之间的一段对话替代了一家人游玩影像的声轨,那是她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到和想到的。对父母而言,不曾见过的大海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又为何总是提起死亡?在这些通过沟通无法穿透的疑问中,和伙伴的对话和反思让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状态变得更为立体和复杂。《35号公墓》的导演面对不再透露更多的父母,选择剑走偏锋:述诸历史的宏大叙事,他把家庭故事汇合进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背景,在其中侦探早逝姐姐身世、乃至整个家族的蛛丝马迹。在《日常对话》中,面对家族长辈对母亲秘密的三缄其口,黄惠侦直接向他们发起进攻,她追问:既然你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怎么这么冷静」?此时的镜头凝滞,所有的表情、眼神、小动作都在里面。面对不愿谈论自己「不是秘密的秘密」的母亲,黄也不依不饶,前一秒仍拒绝沟通的母亲,后一秒都被自己「带女生回家却不愿谈论」的悖谬惹笑了。通过不断展现过往的DV,展现女朋友们和亲人不断地谈论,以及他们面对禁忌的不同态度,她鼓起勇气揭开自己秘密和创伤,而所有这些难道不也是为了让母亲和观众直面伤痛所作的准备吗。沟通之不可能在这些影像中最终都没有被消解,相反,纪录片作者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将冲突转为张力。正是在个意义上,私密性的影像有了普遍性的联结点,对观众而言,情感的冲击和扰动不仅仅指向了他自身的处境和记忆,也打开了公共性的维度: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究竟如何相处。《我母亲的消失》中「战争」和游戏诚然呈现了母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影像策略的思考上贝尼安米有着自己的一贯性:无论是作为儿子观察母亲,还是客观地观察模特、教育者贝内黛塔,基本上他采取了贝内黛塔所反对的将被摄者牢牢固定在图像之中的方式。影片皆大欢喜的结尾也是如此,十分讨巧安排由母亲「掌控」一次摄影机,似乎让这个影像游戏更具辩证意味。实际上,结尾虚拟了母亲在海面上漂流,并准备驶向某个无人之处,无非是再次将母亲「消失」这一行为收入自己的「玩具收藏盒」中。导演当真如他所言的理解了母亲吗?这难道没有表现出一种对情感羁绊、亲密关系的错误理解和幼稚态度:它们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解和认同之上,而只有如此我们才有话可说。根本没有这种必要,需要的只有倾听。贝内黛塔在几处访谈中都明确表示,她既不曾享受过60年代任何一次拍摄,也不曾喜欢纽约这座城市,即便受到过肯尼迪家族这样的名门邀请,在聚会上她也只不过是像洋娃娃一样的玩弄对象,这一切都不好受。[8] 她是否认为将来会有更道德的时尚产业出现?「不会。或许再过两百年。」——这是原话[9]。 对于《我母亲的消失》更实际的不满和担忧是,事实上,有更多人(比如女权主义者)会和贝内黛塔产生并不存在沟通的联结或共通,从一些观众对影片的评论中显然已经能够看出这点。在荧幕之外,人们比导演更多地体会到了贝内黛塔所期望的「消失/消隐」的涵义,正如我们知道莉拉从未消失一样,她只是走进黑夜之中。就像《失踪的孩子》中的最后一行——莱农想着:「现在莉拉那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我应该放弃继续找她。」[1] 参见纪录片《费兰特热潮》(Ferrante Fever,2017)中对弗兰岑的访谈。[2] 参见《我母亲的消失》官方网站(https://www.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com/)的导演手记。[3] 参见“The Boldly Heroic Benedetta Barzini: Marxist, Model and Muse”,作者Sophie Bew。https://www.anothermag.com/fashion-beauty/10099/the-boldly-heroic-benedetta-barzini-marxist-model-and-muse[4] 参见导演访谈“The Camera Is Evil in Sundance’s ‘The Disappearance of My Mother’”。https://nofilmschool.com/2020/01/disappearance-my-mother-sundance[5] 参见官方网站导演手记。[6] 参见《美丽的标价》“第二章 T台经济学”,阿什利·米尔斯著,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引自《美国独立电影》,约翰·贝拉主编,朱鸿飞、萧达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参见“Benedetta Barzini On The Art Of Ageing Gracefully”,https://www.vogue.co.uk/article/benedetta-barzini-on-ageing,以及访谈“New York’s unreciprocated love for Benedetta Barzini”,https://www.documentjournal.com/2018/10/new-yorks-unreciprocated-love-for-benedetta-barzini/。[9] 参见贝内黛塔和《Interview》杂志的访谈:“The Disappearing Act of Benedetta Barzini”,采访人:Conor Williams,https://www.interviewmagazine.com/film/benedetta-barzini-the-disappearance-of-my-mother-beniamino-barrese。——原载于「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公众号」——"<>"暂时没有网友评论该影片"}{end 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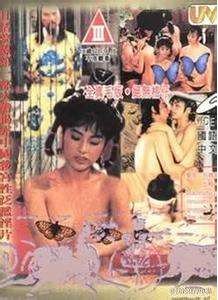

母親失格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