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剧情简介:一个年轻的孤儿在泰国农村长大,她的祖母教她魔术的方法。但是当祖母生病时,Dau被引诱到曼谷去找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买药了。她发觉自己在一家活跃的酒吧工作,她从天真到成熟的旅程是迅速的。她利用了祖母教给她的魔法技能,但这样做却在酒吧里树敌。随着她的魔法越来越黑暗,结果越来越可怕,她逐渐失去控制,邪恶的东西接管了。 如今,电影已经成熟到不论使用长镜头还是短镜头都不会有太大障碍。希区柯克《绳索》的技术开创时代已经过去。安哲罗普罗斯在一个镜头里划过几十年的调度法初见时也实在叫人恨不得把情绪永远抛在那时间的荒野上。《鸟人》的摄影指导Emmanuel Lubezkis将近十年前在《人类之子》里的复杂长镜头调度出来的时候,还可以令人惊异一番。而去年,复杂的长镜头调度已经被他在《地心引力》里应用到宇宙空间里去了。
今天,导演什么极端效果都能拍得出来,观众也什么极端效果都吞得下去。在这种双方的感觉神经都进化到麻木的情况下,一镜到底的美学实验意义已经丧尽,甚至连炫技也算不上。而好莱坞滥用一切的秉性极有效率地使得一切迅速变为陈腔滥调。如今看到一个两小时的长镜头,感觉和看到已泛滥的《碟影重重》式的快速剪辑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取用长镜头就必须更为谨慎。倘若技术之下的故事或情绪本身不够强大,那么技巧越高,也不过是使一具僵尸之躯运行得更为灵活。
幸好导演伊纳里图提供了足够丰满的血肉,演员提供了足够有爆发力的筋骨,而卡弗与超级英雄提供了一个纠结的灵魂。
《鸟人》的主要故事在一个镜头中发生。过气的演员里根·汤姆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出演过超级英雄电影角色:鸟侠。(饰演汤姆森的是迈克尔·基顿,曾经的蝙蝠侠。)
二十年过去,好像几个世纪过去了,被新时代抛弃的汤姆森在百老汇的一间老戏院排起了一出戏剧,这出戏改编自卡弗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由他自导自演。排这出戏的目的,是汤姆森作为一个演员,决计要在自己的表演事业中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好莱坞演超级英雄片太过出名,他的事业迅速被赶时髦的观众遗忘,平庸得一塌糊涂。
卡弗的小说是寻找意义最好的地界,那里没有情节,踏进去就是踏进情感的泥潭。这也是影片最大的讽刺,汤姆森脑中那个不知何时就会冒出来的超级英雄第二人格时时提醒他好莱坞的荣光与力量,而百老汇戏剧舞台上的严肃戏剧时时告诉他这个世界的无力与荒唐。
汤姆森带着在典型的好莱坞励志片式的“寻找意义”的目的来到百老汇,而后跌入无意义的深渊。整部影片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的,或者说无意义的怪圈。
我至今记得卡弗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个冰箱的坏掉,食物溢出难以言喻的脏水。小说里人们的关系也像进入了一个坏掉的冰箱,腐败而变质。
罗伯特·奥尔特曼改编卡弗时,用的是伊纳里图也擅长的独立而交织的多线索叙事,并展现出一幅群戏的大画卷,在奥尔特曼那更多广角镜头的风格中,八组人物互为背景,互相纠结。
伊纳里图并没有改编卡弗,但他不可避免地将卡弗的人物关系精神引入到电影中。影片中那个逼仄的戏院就是一个坏掉的人际关系冰箱,处处散发着细菌式的危险气息。
伊纳里图放弃了多线索叙事,但《鸟人》完全没有绕着传统的单线索情节跳大绳。汤姆森是主线,然而使他的形象完全立起来的,是他身边所有那些爱他,同时也恨他入骨的角色们。影片镜头永远不会放弃从汤姆森脸部那些迷惘的沟壑里游移开来,向另一个角色的脸上去凝视。而后这个镜头也总是会带着另一个角色的情绪向汤姆森迅疾地侵袭。譬如他女儿对他的愤恨与和解,爱德华·诺顿饰演的知名戏剧演员麦克对他的精神虐待与角斗,他前妻对他的怒火与怜爱,与他排戏的女演员对他的愤懑与无可奈何,百老汇老女人评论家对他的宣战,他那个“鸟侠”的分身对他施加的让他去“飞起来”的压力……
伊纳里图最大的实验,就是在“一个长镜头”中推进情节的生活线索的同时,把这么多情绪的线索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而将情绪深深刻入人心的工具,是那些推近到令人难以呼吸的面部大特写。
伊纳里图在人物之间塑造了卡弗式的如食物变质一般的悲凉关系,但他又在卡弗封闭的人物心理世界中凿开了门与窗。灼烧汤姆森的,不仅仅是将崩溃的爱情与亲情,还有随时代变幻的强光。
汤姆森在戏台上对着戏中不爱他的妻子喃喃自语:“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在“古老”的卡弗时代,人感到自己不存在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与变异。而他的女儿告诉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没有智能手机,他“根本不存在”。
被女儿痛骂一顿之后,我们看见汤姆森以超能力转动了桌子上的一只金属烟盒,他只能在旧日主演的电影中找到一点存在感的灰烬。我们看到他点烟时烫到了手,存在感在他滑稽的抖手动作中迅速消失了。
同样的手法在汤姆森幻想自己飞翔的时候再次出现,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睡在了街头的垃圾袋上,醒来之后,鸟侠的幻想开始膨胀,于是他在城市上空飞了起来,一直飞回了戏院,而后镜头停留在在戏院门口的街道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下车,奔进戏院找他要车钱。
这次飞翔是电影的一个高潮,是汤姆森好莱坞超级英雄梦的最后一次勃起。之后,痛苦至极的他将在舞台上用真枪换掉道具枪,面对观众枪毙自己。
但自杀不成功,鸟人轰掉了自己的鼻子。自杀壮举的意义被否定了,“意义”化身为电视中无数为汤姆森点蜡烛的人群,同时也化身为她女儿为他设立的twitter账号中一天内获得的八千个的粉丝。他的演出被媒体盛赞,在“鸟侠”时代的大明星名声似乎又将回到汤姆森的身上。但没有人知道是这耸动就的行为还真的是他的演技换回了这名声。唯一的胜利是,这个行为使汤姆森以血腥的手段击溃了那个似乎还活在报纸时代的评论家,社交网络时代所有的选票都投给了汤姆森。
但汤姆森自己并没有感到寻找到意义的如释重负。整部影片中,他的存在,一直在一个超级英雄演员和一个“有意义”的演员之间摇摆。他脑中的分身告诉他票房排行榜是存在,他自己告诉老婆,这出百老汇的戏才是他真正的存在。而在他已经轰掉了自己的老鼻子,装上了怪异的新鼻子时,他发现一切的意义似乎都不那么大了,他在获得亲情的和解之后从窗户跃了出去。
从他女儿的笑容里我们知道他飞了起来。但也许又是说他获得了解脱抵达了彼岸。导演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这最后的飞翔,也只是穿着病服的纵身一跃,飞翔的姿态或根本没有飞起来的姿态,只能靠我们卑微的想象去填补。
大多数电影都致力于成为意义的庆功会,而伊纳里图则通过过于沉痛的幽默一步一步打造出意义的葬礼。影片最后一闪而过的那个奇怪的生物就像费里尼《甜蜜生活》最后那个黄色小报记者在海滩上看到的奇怪的大鱼。它与影片开始与结束时天空划过的火球一样,成为无意义的高档标签。
汤姆森枪毙自己的行为发生的同时,他也为自己脑中时刻要膨胀的超级英雄的“分身”判了死刑。自我枪毙的行为发生之后,长镜头结束了。百老汇那间戏院的舞台上,蜘蛛侠,变形金刚,美国队长由穿着拙劣的戏服的演员扮演,他们在拙劣的灯光中互相殴打,围着他们的是几个扮作狂欢游行队列的打鼓人。超级英雄的实质被道出。
在汤姆森脑中一直盘旋的鸟人角色的潜意识终于闭上了嘴。
终于,六十年前的小说张开淌着脏水的嘴巴,吞掉了"蝙蝠侠"虚妄的斗篷,也就是鸟侠的翅膀
——卡弗干掉了蝙蝠侠。
今天,导演什么极端效果都能拍得出来,观众也什么极端效果都吞得下去。在这种双方的感觉神经都进化到麻木的情况下,一镜到底的美学实验意义已经丧尽,甚至连炫技也算不上。而好莱坞滥用一切的秉性极有效率地使得一切迅速变为陈腔滥调。如今看到一个两小时的长镜头,感觉和看到已泛滥的《碟影重重》式的快速剪辑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取用长镜头就必须更为谨慎。倘若技术之下的故事或情绪本身不够强大,那么技巧越高,也不过是使一具僵尸之躯运行得更为灵活。
幸好导演伊纳里图提供了足够丰满的血肉,演员提供了足够有爆发力的筋骨,而卡弗与超级英雄提供了一个纠结的灵魂。
《鸟人》的主要故事在一个镜头中发生。过气的演员里根·汤姆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出演过超级英雄电影角色:鸟侠。(饰演汤姆森的是迈克尔·基顿,曾经的蝙蝠侠。)
二十年过去,好像几个世纪过去了,被新时代抛弃的汤姆森在百老汇的一间老戏院排起了一出戏剧,这出戏改编自卡弗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由他自导自演。排这出戏的目的,是汤姆森作为一个演员,决计要在自己的表演事业中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好莱坞演超级英雄片太过出名,他的事业迅速被赶时髦的观众遗忘,平庸得一塌糊涂。
卡弗的小说是寻找意义最好的地界,那里没有情节,踏进去就是踏进情感的泥潭。这也是影片最大的讽刺,汤姆森脑中那个不知何时就会冒出来的超级英雄第二人格时时提醒他好莱坞的荣光与力量,而百老汇戏剧舞台上的严肃戏剧时时告诉他这个世界的无力与荒唐。
汤姆森带着在典型的好莱坞励志片式的“寻找意义”的目的来到百老汇,而后跌入无意义的深渊。整部影片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的,或者说无意义的怪圈。
我至今记得卡弗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个冰箱的坏掉,食物溢出难以言喻的脏水。小说里人们的关系也像进入了一个坏掉的冰箱,腐败而变质。
罗伯特·奥尔特曼改编卡弗时,用的是伊纳里图也擅长的独立而交织的多线索叙事,并展现出一幅群戏的大画卷,在奥尔特曼那更多广角镜头的风格中,八组人物互为背景,互相纠结。
伊纳里图并没有改编卡弗,但他不可避免地将卡弗的人物关系精神引入到电影中。影片中那个逼仄的戏院就是一个坏掉的人际关系冰箱,处处散发着细菌式的危险气息。
伊纳里图放弃了多线索叙事,但《鸟人》完全没有绕着传统的单线索情节跳大绳。汤姆森是主线,然而使他的形象完全立起来的,是他身边所有那些爱他,同时也恨他入骨的角色们。影片镜头永远不会放弃从汤姆森脸部那些迷惘的沟壑里游移开来,向另一个角色的脸上去凝视。而后这个镜头也总是会带着另一个角色的情绪向汤姆森迅疾地侵袭。譬如他女儿对他的愤恨与和解,爱德华·诺顿饰演的知名戏剧演员麦克对他的精神虐待与角斗,他前妻对他的怒火与怜爱,与他排戏的女演员对他的愤懑与无可奈何,百老汇老女人评论家对他的宣战,他那个“鸟侠”的分身对他施加的让他去“飞起来”的压力……
伊纳里图最大的实验,就是在“一个长镜头”中推进情节的生活线索的同时,把这么多情绪的线索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而将情绪深深刻入人心的工具,是那些推近到令人难以呼吸的面部大特写。
伊纳里图在人物之间塑造了卡弗式的如食物变质一般的悲凉关系,但他又在卡弗封闭的人物心理世界中凿开了门与窗。灼烧汤姆森的,不仅仅是将崩溃的爱情与亲情,还有随时代变幻的强光。
汤姆森在戏台上对着戏中不爱他的妻子喃喃自语:“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在“古老”的卡弗时代,人感到自己不存在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与变异。而他的女儿告诉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没有智能手机,他“根本不存在”。
被女儿痛骂一顿之后,我们看见汤姆森以超能力转动了桌子上的一只金属烟盒,他只能在旧日主演的电影中找到一点存在感的灰烬。我们看到他点烟时烫到了手,存在感在他滑稽的抖手动作中迅速消失了。
同样的手法在汤姆森幻想自己飞翔的时候再次出现,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睡在了街头的垃圾袋上,醒来之后,鸟侠的幻想开始膨胀,于是他在城市上空飞了起来,一直飞回了戏院,而后镜头停留在在戏院门口的街道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下车,奔进戏院找他要车钱。
这次飞翔是电影的一个高潮,是汤姆森好莱坞超级英雄梦的最后一次勃起。之后,痛苦至极的他将在舞台上用真枪换掉道具枪,面对观众枪毙自己。
但自杀不成功,鸟人轰掉了自己的鼻子。自杀壮举的意义被否定了,“意义”化身为电视中无数为汤姆森点蜡烛的人群,同时也化身为她女儿为他设立的twitter账号中一天内获得的八千个的粉丝。他的演出被媒体盛赞,在“鸟侠”时代的大明星名声似乎又将回到汤姆森的身上。但没有人知道是这耸动就的行为还真的是他的演技换回了这名声。唯一的胜利是,这个行为使汤姆森以血腥的手段击溃了那个似乎还活在报纸时代的评论家,社交网络时代所有的选票都投给了汤姆森。
但汤姆森自己并没有感到寻找到意义的如释重负。整部影片中,他的存在,一直在一个超级英雄演员和一个“有意义”的演员之间摇摆。他脑中的分身告诉他票房排行榜是存在,他自己告诉老婆,这出百老汇的戏才是他真正的存在。而在他已经轰掉了自己的老鼻子,装上了怪异的新鼻子时,他发现一切的意义似乎都不那么大了,他在获得亲情的和解之后从窗户跃了出去。
从他女儿的笑容里我们知道他飞了起来。但也许又是说他获得了解脱抵达了彼岸。导演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这最后的飞翔,也只是穿着病服的纵身一跃,飞翔的姿态或根本没有飞起来的姿态,只能靠我们卑微的想象去填补。
大多数电影都致力于成为意义的庆功会,而伊纳里图则通过过于沉痛的幽默一步一步打造出意义的葬礼。影片最后一闪而过的那个奇怪的生物就像费里尼《甜蜜生活》最后那个黄色小报记者在海滩上看到的奇怪的大鱼。它与影片开始与结束时天空划过的火球一样,成为无意义的高档标签。
汤姆森枪毙自己的行为发生的同时,他也为自己脑中时刻要膨胀的超级英雄的“分身”判了死刑。自我枪毙的行为发生之后,长镜头结束了。百老汇那间戏院的舞台上,蜘蛛侠,变形金刚,美国队长由穿着拙劣的戏服的演员扮演,他们在拙劣的灯光中互相殴打,围着他们的是几个扮作狂欢游行队列的打鼓人。超级英雄的实质被道出。
在汤姆森脑中一直盘旋的鸟人角色的潜意识终于闭上了嘴。
终于,六十年前的小说张开淌着脏水的嘴巴,吞掉了"蝙蝠侠"虚妄的斗篷,也就是鸟侠的翅膀
——卡弗干掉了蝙蝠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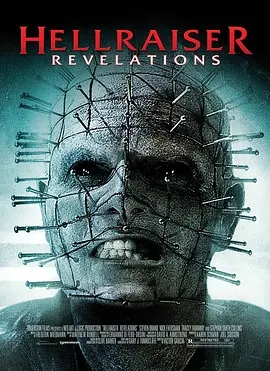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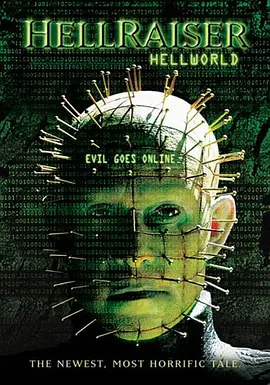




P魔力影评
今天,导演什么极端效果都能拍得出来,观众也什么极端效果都吞得下去。在这种双方的感觉神经都进化到麻木的情况下,一镜到底的美学实验意义已经丧尽,甚至连炫技也算不上。而好莱坞滥用一切的秉性极有效率地使得一切迅速变为陈腔滥调。如今看到一个两小时的长镜头,感觉和看到已泛滥的《碟影重重》式的快速剪辑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取用长镜头就必须更为谨慎。倘若技术之下的故事或情绪本身不够强大,那么技巧越高,也不过是使一具僵尸之躯运行得更为灵活。
幸好导演伊纳里图提供了足够丰满的血肉,演员提供了足够有爆发力的筋骨,而卡弗与超级英雄提供了一个纠结的灵魂。
《鸟人》的主要故事在一个镜头中发生。过气的演员里根·汤姆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出演过超级英雄电影角色:鸟侠。(饰演汤姆森的是迈克尔·基顿,曾经的蝙蝠侠。)
二十年过去,好像几个世纪过去了,被新时代抛弃的汤姆森在百老汇的一间老戏院排起了一出戏剧,这出戏改编自卡弗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由他自导自演。排这出戏的目的,是汤姆森作为一个演员,决计要在自己的表演事业中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好莱坞演超级英雄片太过出名,他的事业迅速被赶时髦的观众遗忘,平庸得一塌糊涂。
卡弗的小说是寻找意义最好的地界,那里没有情节,踏进去就是踏进情感的泥潭。这也是影片最大的讽刺,汤姆森脑中那个不知何时就会冒出来的超级英雄第二人格时时提醒他好莱坞的荣光与力量,而百老汇戏剧舞台上的严肃戏剧时时告诉他这个世界的无力与荒唐。
汤姆森带着在典型的好莱坞励志片式的“寻找意义”的目的来到百老汇,而后跌入无意义的深渊。整部影片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的,或者说无意义的怪圈。
我至今记得卡弗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个冰箱的坏掉,食物溢出难以言喻的脏水。小说里人们的关系也像进入了一个坏掉的冰箱,腐败而变质。
罗伯特·奥尔特曼改编卡弗时,用的是伊纳里图也擅长的独立而交织的多线索叙事,并展现出一幅群戏的大画卷,在奥尔特曼那更多广角镜头的风格中,八组人物互为背景,互相纠结。
伊纳里图并没有改编卡弗,但他不可避免地将卡弗的人物关系精神引入到电影中。影片中那个逼仄的戏院就是一个坏掉的人际关系冰箱,处处散发着细菌式的危险气息。
伊纳里图放弃了多线索叙事,但《鸟人》完全没有绕着传统的单线索情节跳大绳。汤姆森是主线,然而使他的形象完全立起来的,是他身边所有那些爱他,同时也恨他入骨的角色们。影片镜头永远不会放弃从汤姆森脸部那些迷惘的沟壑里游移开来,向另一个角色的脸上去凝视。而后这个镜头也总是会带着另一个角色的情绪向汤姆森迅疾地侵袭。譬如他女儿对他的愤恨与和解,爱德华·诺顿饰演的知名戏剧演员麦克对他的精神虐待与角斗,他前妻对他的怒火与怜爱,与他排戏的女演员对他的愤懑与无可奈何,百老汇老女人评论家对他的宣战,他那个“鸟侠”的分身对他施加的让他去“飞起来”的压力……
伊纳里图最大的实验,就是在“一个长镜头”中推进情节的生活线索的同时,把这么多情绪的线索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而将情绪深深刻入人心的工具,是那些推近到令人难以呼吸的面部大特写。
伊纳里图在人物之间塑造了卡弗式的如食物变质一般的悲凉关系,但他又在卡弗封闭的人物心理世界中凿开了门与窗。灼烧汤姆森的,不仅仅是将崩溃的爱情与亲情,还有随时代变幻的强光。
汤姆森在戏台上对着戏中不爱他的妻子喃喃自语:“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在“古老”的卡弗时代,人感到自己不存在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与变异。而他的女儿告诉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没有智能手机,他“根本不存在”。
被女儿痛骂一顿之后,我们看见汤姆森以超能力转动了桌子上的一只金属烟盒,他只能在旧日主演的电影中找到一点存在感的灰烬。我们看到他点烟时烫到了手,存在感在他滑稽的抖手动作中迅速消失了。
同样的手法在汤姆森幻想自己飞翔的时候再次出现,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睡在了街头的垃圾袋上,醒来之后,鸟侠的幻想开始膨胀,于是他在城市上空飞了起来,一直飞回了戏院,而后镜头停留在在戏院门口的街道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下车,奔进戏院找他要车钱。
这次飞翔是电影的一个高潮,是汤姆森好莱坞超级英雄梦的最后一次勃起。之后,痛苦至极的他将在舞台上用真枪换掉道具枪,面对观众枪毙自己。
但自杀不成功,鸟人轰掉了自己的鼻子。自杀壮举的意义被否定了,“意义”化身为电视中无数为汤姆森点蜡烛的人群,同时也化身为她女儿为他设立的twitter账号中一天内获得的八千个的粉丝。他的演出被媒体盛赞,在“鸟侠”时代的大明星名声似乎又将回到汤姆森的身上。但没有人知道是这耸动就的行为还真的是他的演技换回了这名声。唯一的胜利是,这个行为使汤姆森以血腥的手段击溃了那个似乎还活在报纸时代的评论家,社交网络时代所有的选票都投给了汤姆森。
但汤姆森自己并没有感到寻找到意义的如释重负。整部影片中,他的存在,一直在一个超级英雄演员和一个“有意义”的演员之间摇摆。他脑中的分身告诉他票房排行榜是存在,他自己告诉老婆,这出百老汇的戏才是他真正的存在。而在他已经轰掉了自己的老鼻子,装上了怪异的新鼻子时,他发现一切的意义似乎都不那么大了,他在获得亲情的和解之后从窗户跃了出去。
从他女儿的笑容里我们知道他飞了起来。但也许又是说他获得了解脱抵达了彼岸。导演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这最后的飞翔,也只是穿着病服的纵身一跃,飞翔的姿态或根本没有飞起来的姿态,只能靠我们卑微的想象去填补。
大多数电影都致力于成为意义的庆功会,而伊纳里图则通过过于沉痛的幽默一步一步打造出意义的葬礼。影片最后一闪而过的那个奇怪的生物就像费里尼《甜蜜生活》最后那个黄色小报记者在海滩上看到的奇怪的大鱼。它与影片开始与结束时天空划过的火球一样,成为无意义的高档标签。
汤姆森枪毙自己的行为发生的同时,他也为自己脑中时刻要膨胀的超级英雄的“分身”判了死刑。自我枪毙的行为发生之后,长镜头结束了。百老汇那间戏院的舞台上,蜘蛛侠,变形金刚,美国队长由穿着拙劣的戏服的演员扮演,他们在拙劣的灯光中互相殴打,围着他们的是几个扮作狂欢游行队列的打鼓人。超级英雄的实质被道出。
在汤姆森脑中一直盘旋的鸟人角色的潜意识终于闭上了嘴。
终于,六十年前的小说张开淌着脏水的嘴巴,吞掉了"蝙蝠侠"虚妄的斗篷,也就是鸟侠的翅膀
——卡弗干掉了蝙蝠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