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剧情介绍:影片以养蜂人斯皮罗的女儿非常平淡的婚礼开场。婚礼结束后,斯皮罗仍然跟随养蜂人的队伍在南方放养蜜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浪,所以他准备告别家人,从此一个人呆着。在途中。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因搭便车而失恋的女孩,他好心让那个无处可去的女孩在酒店住了一晚。继续在路上,他遇到了儿时的玩伴。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同时,他在少女的青春张扬和活力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确定性。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产生了“老爷子聊”少年狂”的冲动。当然,重逢是昙花一现。当女孩再次上路的时候,斯皮罗心中的悲伤太多了。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依附的,所以他在阳光下打开了所有的蜂箱...... .----kavkalu电影开始后的第一秒种,第一条字幕就出现了,不是电影的片名,不是导演的名字,而是简单的两个单词:Marcello Mastroianni,是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曾经是费里尼的马斯楚安尼,德西卡的马斯楚安尼,安东尼奥尼的马斯楚安尼,现在,是安哲罗普洛斯的马斯楚安尼。
1959年,马斯楚安尼35岁。
那一年,以《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连拿两个奥斯卡小金人的费里尼,决定拍点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后来的《甜蜜的生活》。费里尼找到了当时已是意大利天王巨星的马斯楚安尼,费大师对马天王说:“跟你打电话,是因为我需要一张没有一点个性的脸,比如你这样的。”马天王哭笑不得,但依然答应出演。
从此,马天王不再是意大利的天王。
1986年,马斯楚安尼已经62岁,比起《甜蜜的生活》时,他有些发福,也有些驼背,甚至还留了一个斯大林式的胡须。他不再是《甜蜜的生活》里的报社记者马塞洛,也不再是《八部半》里的导演吉多,但他依然是那个拥有着“一张没有任何个性的脸”的马斯楚安尼,他的忧郁、凄楚、放荡、孤独、迷茫、矛盾、困惑、沉默、绝望、黯然、神秘、颓废、空虚、堕落、敏感,和一切,混织在一起,铺满在这张复印纸般的脸上。
所以斯皮罗也就继承了马塞洛和吉多的一切,尽管他有家庭有女儿,甚至他的女儿刚刚举办了一场难忘的婚礼。但他依然是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孤独者。
所以斯皮罗去旅行。
为什么选择旅行?安哲的另一部电影《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已经给出了答案:“上帝首先创造了旅行,而后是怀疑和思乡。”旅行、怀疑和思乡是贯穿了安哲一生的电影命题,身体和生命的旅行,对存在和生活的怀疑,对精神故乡的向往与追寻。
旅行是让生命充满未知的方式,因为旅程中总是能看到新鲜的风景,遇到或新或旧的人,所以斯皮罗就遇到了那个女孩。女孩说:“随便去哪里,只要离开这”。与“去日无多”的斯皮罗相比,女孩“譬如朝露”,她年轻、放纵、我行我素,随遇而安,她在音乐机前独自疯狂劲舞,她从斯皮罗的口袋里掏钱买烟,她咬斯皮罗的手直到鲜血淋漓,她在斯皮罗的房间同另一个男人做爱,她把青春注入到斯皮罗老朽的肌体,她用年轻,救赎着这个衰老男人早已麻木的生命。于是斯皮罗驾着蜂车冲破了酒吧,她在一片狼藉中跳上车,他们扬长而去。天哪!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浪漫镜头。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剧场,在空寂的舞台上华丽的做爱,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马龙•白兰度和玛利亚•施奈德那样。火车在他们身边隆隆的驶过。侯孝贤电影里的火车总是寓意着无限伸向远方的希望,而火车之于安哲,则只有彻底的绝望。当斯皮罗进入女孩的身体时,女孩忘情的嘶喊着“让我飞翔!让我飞翔!”,于是她就真的飞走了,斯皮罗从来就不是她生命的终点,甚至连站台都不是,她只是“碰巧路过”。
世界其实是一个大蜂箱,拥挤而沉闷,斯皮罗是蜂箱里一只痛苦的蜜蜂,他无法拒绝命运,他抗争,但万事不由己。从没有人真正在意他,甚至是同他一起旅行的女孩。他孤独、绝望、无可奈何。
他终于掀翻了蜂箱,把自己一路上的关怀与珍惜掀了个底朝天,也与一生中最后的珍惜宣告了再见,就像马斯楚安尼向凯瑟琳•德诺芙说再见。蜂儿弥漫,他倒下,双手狂舞。此时,我早已分不清屏幕上的人到底是斯皮罗,还是马斯楚安尼,他们似乎已经合身一体,捕捉着自己逝去的青春。
马斯楚安尼的晚年,他总是神情恍惚,他日复一日的向身边的人讲述着费里尼和他的初遇,和费里尼对他脸的评价,他总是悄悄的说:“嘘,我来自费里尼的电影,我不是真的。”
是的,他一生拍了140多部电影,但他只来自费里尼的电影,因为那是他不朽的青春。
愿我们都能有一个不朽的青春。
1959年,马斯楚安尼35岁。
那一年,以《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连拿两个奥斯卡小金人的费里尼,决定拍点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后来的《甜蜜的生活》。费里尼找到了当时已是意大利天王巨星的马斯楚安尼,费大师对马天王说:“跟你打电话,是因为我需要一张没有一点个性的脸,比如你这样的。”马天王哭笑不得,但依然答应出演。
从此,马天王不再是意大利的天王。
1986年,马斯楚安尼已经62岁,比起《甜蜜的生活》时,他有些发福,也有些驼背,甚至还留了一个斯大林式的胡须。他不再是《甜蜜的生活》里的报社记者马塞洛,也不再是《八部半》里的导演吉多,但他依然是那个拥有着“一张没有任何个性的脸”的马斯楚安尼,他的忧郁、凄楚、放荡、孤独、迷茫、矛盾、困惑、沉默、绝望、黯然、神秘、颓废、空虚、堕落、敏感,和一切,混织在一起,铺满在这张复印纸般的脸上。
所以斯皮罗也就继承了马塞洛和吉多的一切,尽管他有家庭有女儿,甚至他的女儿刚刚举办了一场难忘的婚礼。但他依然是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孤独者。
所以斯皮罗去旅行。
为什么选择旅行?安哲的另一部电影《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已经给出了答案:“上帝首先创造了旅行,而后是怀疑和思乡。”旅行、怀疑和思乡是贯穿了安哲一生的电影命题,身体和生命的旅行,对存在和生活的怀疑,对精神故乡的向往与追寻。
旅行是让生命充满未知的方式,因为旅程中总是能看到新鲜的风景,遇到或新或旧的人,所以斯皮罗就遇到了那个女孩。女孩说:“随便去哪里,只要离开这”。与“去日无多”的斯皮罗相比,女孩“譬如朝露”,她年轻、放纵、我行我素,随遇而安,她在音乐机前独自疯狂劲舞,她从斯皮罗的口袋里掏钱买烟,她咬斯皮罗的手直到鲜血淋漓,她在斯皮罗的房间同另一个男人做爱,她把青春注入到斯皮罗老朽的肌体,她用年轻,救赎着这个衰老男人早已麻木的生命。于是斯皮罗驾着蜂车冲破了酒吧,她在一片狼藉中跳上车,他们扬长而去。天哪!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浪漫镜头。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剧场,在空寂的舞台上华丽的做爱,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马龙•白兰度和玛利亚•施奈德那样。火车在他们身边隆隆的驶过。侯孝贤电影里的火车总是寓意着无限伸向远方的希望,而火车之于安哲,则只有彻底的绝望。当斯皮罗进入女孩的身体时,女孩忘情的嘶喊着“让我飞翔!让我飞翔!”,于是她就真的飞走了,斯皮罗从来就不是她生命的终点,甚至连站台都不是,她只是“碰巧路过”。
世界其实是一个大蜂箱,拥挤而沉闷,斯皮罗是蜂箱里一只痛苦的蜜蜂,他无法拒绝命运,他抗争,但万事不由己。从没有人真正在意他,甚至是同他一起旅行的女孩。他孤独、绝望、无可奈何。
他终于掀翻了蜂箱,把自己一路上的关怀与珍惜掀了个底朝天,也与一生中最后的珍惜宣告了再见,就像马斯楚安尼向凯瑟琳•德诺芙说再见。蜂儿弥漫,他倒下,双手狂舞。此时,我早已分不清屏幕上的人到底是斯皮罗,还是马斯楚安尼,他们似乎已经合身一体,捕捉着自己逝去的青春。
马斯楚安尼的晚年,他总是神情恍惚,他日复一日的向身边的人讲述着费里尼和他的初遇,和费里尼对他脸的评价,他总是悄悄的说:“嘘,我来自费里尼的电影,我不是真的。”
是的,他一生拍了140多部电影,但他只来自费里尼的电影,因为那是他不朽的青春。
愿我们都能有一个不朽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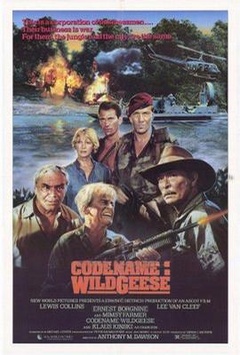





养蜂人影评
1959年,马斯楚安尼35岁。
那一年,以《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连拿两个奥斯卡小金人的费里尼,决定拍点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后来的《甜蜜的生活》。费里尼找到了当时已是意大利天王巨星的马斯楚安尼,费大师对马天王说:“跟你打电话,是因为我需要一张没有一点个性的脸,比如你这样的。”马天王哭笑不得,但依然答应出演。
从此,马天王不再是意大利的天王。
1986年,马斯楚安尼已经62岁,比起《甜蜜的生活》时,他有些发福,也有些驼背,甚至还留了一个斯大林式的胡须。他不再是《甜蜜的生活》里的报社记者马塞洛,也不再是《八部半》里的导演吉多,但他依然是那个拥有着“一张没有任何个性的脸”的马斯楚安尼,他的忧郁、凄楚、放荡、孤独、迷茫、矛盾、困惑、沉默、绝望、黯然、神秘、颓废、空虚、堕落、敏感,和一切,混织在一起,铺满在这张复印纸般的脸上。
所以斯皮罗也就继承了马塞洛和吉多的一切,尽管他有家庭有女儿,甚至他的女儿刚刚举办了一场难忘的婚礼。但他依然是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孤独者。
所以斯皮罗去旅行。
为什么选择旅行?安哲的另一部电影《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已经给出了答案:“上帝首先创造了旅行,而后是怀疑和思乡。”旅行、怀疑和思乡是贯穿了安哲一生的电影命题,身体和生命的旅行,对存在和生活的怀疑,对精神故乡的向往与追寻。
旅行是让生命充满未知的方式,因为旅程中总是能看到新鲜的风景,遇到或新或旧的人,所以斯皮罗就遇到了那个女孩。女孩说:“随便去哪里,只要离开这”。与“去日无多”的斯皮罗相比,女孩“譬如朝露”,她年轻、放纵、我行我素,随遇而安,她在音乐机前独自疯狂劲舞,她从斯皮罗的口袋里掏钱买烟,她咬斯皮罗的手直到鲜血淋漓,她在斯皮罗的房间同另一个男人做爱,她把青春注入到斯皮罗老朽的肌体,她用年轻,救赎着这个衰老男人早已麻木的生命。于是斯皮罗驾着蜂车冲破了酒吧,她在一片狼藉中跳上车,他们扬长而去。天哪!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浪漫镜头。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剧场,在空寂的舞台上华丽的做爱,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马龙•白兰度和玛利亚•施奈德那样。火车在他们身边隆隆的驶过。侯孝贤电影里的火车总是寓意着无限伸向远方的希望,而火车之于安哲,则只有彻底的绝望。当斯皮罗进入女孩的身体时,女孩忘情的嘶喊着“让我飞翔!让我飞翔!”,于是她就真的飞走了,斯皮罗从来就不是她生命的终点,甚至连站台都不是,她只是“碰巧路过”。
世界其实是一个大蜂箱,拥挤而沉闷,斯皮罗是蜂箱里一只痛苦的蜜蜂,他无法拒绝命运,他抗争,但万事不由己。从没有人真正在意他,甚至是同他一起旅行的女孩。他孤独、绝望、无可奈何。
他终于掀翻了蜂箱,把自己一路上的关怀与珍惜掀了个底朝天,也与一生中最后的珍惜宣告了再见,就像马斯楚安尼向凯瑟琳•德诺芙说再见。蜂儿弥漫,他倒下,双手狂舞。此时,我早已分不清屏幕上的人到底是斯皮罗,还是马斯楚安尼,他们似乎已经合身一体,捕捉着自己逝去的青春。
马斯楚安尼的晚年,他总是神情恍惚,他日复一日的向身边的人讲述着费里尼和他的初遇,和费里尼对他脸的评价,他总是悄悄的说:“嘘,我来自费里尼的电影,我不是真的。”
是的,他一生拍了140多部电影,但他只来自费里尼的电影,因为那是他不朽的青春。
愿我们都能有一个不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