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在这部电影的摄影阐述上,赫然入目地写着这样一句话:“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
《一个和八个》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电影艺术家探索电影的开山之作,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它在电影语言上突破了传统电影语言的范式,表现出了视觉造型的历史个性,这种历史个性有如下特征:首先,它的一切视觉元素、影像造型不再仅只作为故事的叙述手段,而是如同演员,直接传达影片的内涵,为影片的精神现实服务。影片主要描写的不是王金和八个罪犯的外部经历,而是写他们内在心灵的经历,写了灵魂与灵魂的搏斗,人格与人格的撞击。影片设计了女卫生员杨芹儿这个形象,从视觉造型上,让她避免了战争年代那种勇敢、泼辣、风风火火的女性特征,而是强调一种娇嫩的素质,给她穿一件过长的军衣,使其略显柔弱。当长移镜头从另一视角摇过一张张犯人的脸时,我们看到的却是狰狞、野蛮、狠毒和杀气腾腾。尤其他们面部暗淡的阴影,显现出一种紧张的力量的对峙。在紧接着的一个镜头里,前景是几个黑魆魆的巨大人头的背影,两个巨大人头间有一条较大的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卫生员白皙、稚嫩的脸庞。杨芹儿在这里与其作为一个叙事因素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造型因素而存在,她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纯洁的更纯洁,龌龊的更龌龊;柔美的更柔美,粗野的更粗野。影片使用的这一纵深镜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镜头内部蒙太奇的效果。这种蒙太奇暗示着不同灵魂的对比,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白雪与污泥的对比,阳刚与阴柔的对比。通过视觉造型,我们不仅知道了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仁爱与残暴、纯洁与污浊、崇高与渺小、忠贞与叛变之间的冲突,体验到血与火的迸发,生命与生命的撞击。
从画面上看,凡是内景拍摄,无论磨坊、牲口棚还是砖窑,全都是狭小的空间,这与关押在里面的犯人们精神和肉体被扭曲的状况是协调的。在外景拍摄中,尤其在后半部,出现了苍凉、辽阔、空旷的大地和天际,这与他们崇高人格的重新确立,精神生命的重新获得相呼应。
其二,中国中年一代导演在造型上倡导纪实美学,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让银幕最大限度地向生活本貌趋近,可是青年一代导演更着意于艺术个性的展呈和放射,他们的造型在试图表现他们的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表现他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为了把这种感受和体验渲染得强烈深刻,他们有时违反现实的逻辑,做出令人难以意料的艺术处理。例如大秃子打死了三个鬼子后,单手挥舞大枪喊道:“兔崽子们,来吧!……”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他不远处爆炸了,中景镜头里,黑烟笼罩了画面,没过多一会儿,满脸是血的大秃子居然从黑烟里钻出来,嘴里仍旧高喊:“哈哈,痛快!”又是一颗炮弹在他头上炸响,黑烟慢慢地飘散着,等烟全部散尽后,只剩下空空荡荡、干干净净的一片大地。青年艺术家们在视觉的安排上追求了一种诗的风格,让大秃子的人格得到了一种庄严的升华。
其三,影片在造型上追求一种奇特性,力图打破传统造型范式,冲破以往叙事性构图的各种限度:例如这部影片在构图上一般比较饱满,近景、中景居多,被摄物常常占满镜头,给人以撑破画面的印象。影片第一个牢房镜头,用一根根铁杠横贯画面,加上沉郁的色调,给人一种压抑和透不过气的感觉。在拍摄人物对话时,也打破以往电影多用中景镜头及其平衡画面布局的习惯,而是用人的后脑勺或磨盘、箩筐做前景,占满画面的绝大部分,只给说话的人留一点点空间。总之,青年艺术家们在力求总体印象完整的前提下,大胆运用不完整构图,或在画面设计上强调打破平衡,造成异样的视觉刺激,在突出大块面的前提下,用简练手法,造成对比效果。在王金背土匪大秃子通过铁路那个片断里,画面以天空为背景,用降低曝光量的办法把天空压成中级灰,这样所有的人物都成了剪影,并且整场戏都用剪影表现,这是以往电影中不多见的。为了表达的清楚,影片用了每个人不同的身姿、习惯和动作造型,利用每个人讲话时不同的语音语调和咳嗽等,不但使观众看清整个事态的演变,分清每个人物,而且能透过动作窥见人物内心活动。在砖窑那场戏里,王金与犯人们的对立情绪缓和了,双方开始交谈了。在这水井一般的砖窑里,阳光只能从顶部照射进去,创作人员便因势利导,利用窑顶射下来的阳光拍摄。强烈的顶光效果,使人脸在镜头上变形了,甚至难看了。可编导并不回避这种畸变,也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用辅助光冲淡顶光效果,或让光影和造型配合内容中所具有的和解气氛,而是刻意表现视觉造型与内容的对立,故意运用顶光,强调眼窝、面颊、颧骨下的大块阴影,这样形成一种反衬,暗示着他们虽然身陷囹圄,面容丑陋,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心中不乏善良和美好。
其四,这部影片的造型构思,不再是单个画面、单镜头的设想安排,而是注重整个影片造型思维的总体设想,根据全片精神情绪的总的发展,在视像上谋篇布局。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整部影片的色彩显现出蒙太奇结构。影片的前部,以黑色调为主,黑暗的牢房,黑黝肮脏的脸,黑森森的刑场,黑色的主调表达了压抑、沉闷的气氛。影片中部,以红色调为主。在那场突发的遭遇战中,血的洗礼、火的燃烧、红光的爆炸所弥漫、所放射的一点一点、一片一片的红,变成了从黑的压抑走向红的释放的情绪转换。影片的尾部,以白色调为主,这时各种人物走完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历程,找到了各自的归宿,有的人物质生命毁灭了,精神生命却永存了。于是画面上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旷野,明朗灿烂的阳光,辽阔高远的天空。大量的白色调是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象征着升华和新生,全片也走完了由黑到红,由红到白的色彩历程。
其五,这部影片与它之前的中国电影相比,可以说是最具有雕塑感,最富有造型力度的了。为了表现生死存亡中,凝聚血肉,誓死抗敌的民族精神,艺术家们把造型力度作为自己明确的创作追求,他们意识到在所有色彩对比中,黑白对比是最强烈的,所以,他们有意创作出版画般的黑白对比效果。他们还明白,自己所摄录的是一片“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的灾难大地,表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场艰苦斗争,所以任何鲜艳跳跃的色彩都与这一情感意向背道而驰。于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人物服装以黑、白、灰为主,在外景和内景中,避开了所有鲜艳的色彩,在光影安排设计上,内景运用了房屋结构所造成的明暗光区,外景运用强烈阳光造成的亮面和阴影,光线处理中的黑白大反差,强烈地表现了力之美。在摄影机的调度方面,影片不断出现强烈有力的“静态画面”,出现人物雕塑般的造型,例如八个罪犯一张张狰狞、粗野的脸,结尾王金与许志在荒凉大地上顶天屹立的身影,这些线条直硬的静止画面与运动画面相对比而存在,反衬出强烈的力度。
造型的力度还表现在肖像的处理上,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那种不分场合地点,把人物拍得漂漂亮亮、白白嫩嫩的了。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人物脸上粗糙的皮肤,干裂的嘴唇,阴暗牢房里的脏脸,生死搏斗中扭曲的、精瘦的身躯,昏暗光线里破旧的衣衫。这些造型也体现出残酷环境下残酷斗争所迸射出的坚强力度。
《一个和八个》的视觉造型,充分发挥了它的表意、叙事、抒情功能,它的强烈的冲击力,不仅震动了中国影坛,而且揭开了中国当代电影视像造型史上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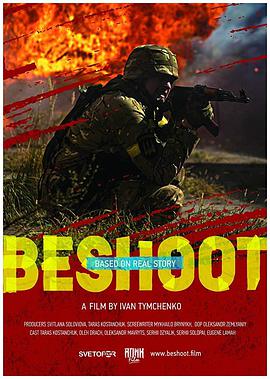










一个和八个影评
在这部电影的摄影阐述上,赫然入目地写着这样一句话:“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
《一个和八个》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电影艺术家探索电影的开山之作,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它在电影语言上突破了传统电影语言的范式,表现出了视觉造型的历史个性,这种历史个性有如下特征:首先,它的一切视觉元素、影像造型不再仅只作为故事的叙述手段,而是如同演员,直接传达影片的内涵,为影片的精神现实服务。影片主要描写的不是王金和八个罪犯的外部经历,而是写他们内在心灵的经历,写了灵魂与灵魂的搏斗,人格与人格的撞击。影片设计了女卫生员杨芹儿这个形象,从视觉造型上,让她避免了战争年代那种勇敢、泼辣、风风火火的女性特征,而是强调一种娇嫩的素质,给她穿一件过长的军衣,使其略显柔弱。当长移镜头从另一视角摇过一张张犯人的脸时,我们看到的却是狰狞、野蛮、狠毒和杀气腾腾。尤其他们面部暗淡的阴影,显现出一种紧张的力量的对峙。在紧接着的一个镜头里,前景是几个黑魆魆的巨大人头的背影,两个巨大人头间有一条较大的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卫生员白皙、稚嫩的脸庞。杨芹儿在这里与其作为一个叙事因素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造型因素而存在,她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纯洁的更纯洁,龌龊的更龌龊;柔美的更柔美,粗野的更粗野。影片使用的这一纵深镜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镜头内部蒙太奇的效果。这种蒙太奇暗示着不同灵魂的对比,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白雪与污泥的对比,阳刚与阴柔的对比。通过视觉造型,我们不仅知道了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仁爱与残暴、纯洁与污浊、崇高与渺小、忠贞与叛变之间的冲突,体验到血与火的迸发,生命与生命的撞击。
从画面上看,凡是内景拍摄,无论磨坊、牲口棚还是砖窑,全都是狭小的空间,这与关押在里面的犯人们精神和肉体被扭曲的状况是协调的。在外景拍摄中,尤其在后半部,出现了苍凉、辽阔、空旷的大地和天际,这与他们崇高人格的重新确立,精神生命的重新获得相呼应。
其二,中国中年一代导演在造型上倡导纪实美学,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让银幕最大限度地向生活本貌趋近,可是青年一代导演更着意于艺术个性的展呈和放射,他们的造型在试图表现他们的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表现他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为了把这种感受和体验渲染得强烈深刻,他们有时违反现实的逻辑,做出令人难以意料的艺术处理。例如大秃子打死了三个鬼子后,单手挥舞大枪喊道:“兔崽子们,来吧!……”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他不远处爆炸了,中景镜头里,黑烟笼罩了画面,没过多一会儿,满脸是血的大秃子居然从黑烟里钻出来,嘴里仍旧高喊:“哈哈,痛快!”又是一颗炮弹在他头上炸响,黑烟慢慢地飘散着,等烟全部散尽后,只剩下空空荡荡、干干净净的一片大地。青年艺术家们在视觉的安排上追求了一种诗的风格,让大秃子的人格得到了一种庄严的升华。
其三,影片在造型上追求一种奇特性,力图打破传统造型范式,冲破以往叙事性构图的各种限度:例如这部影片在构图上一般比较饱满,近景、中景居多,被摄物常常占满镜头,给人以撑破画面的印象。影片第一个牢房镜头,用一根根铁杠横贯画面,加上沉郁的色调,给人一种压抑和透不过气的感觉。在拍摄人物对话时,也打破以往电影多用中景镜头及其平衡画面布局的习惯,而是用人的后脑勺或磨盘、箩筐做前景,占满画面的绝大部分,只给说话的人留一点点空间。总之,青年艺术家们在力求总体印象完整的前提下,大胆运用不完整构图,或在画面设计上强调打破平衡,造成异样的视觉刺激,在突出大块面的前提下,用简练手法,造成对比效果。在王金背土匪大秃子通过铁路那个片断里,画面以天空为背景,用降低曝光量的办法把天空压成中级灰,这样所有的人物都成了剪影,并且整场戏都用剪影表现,这是以往电影中不多见的。为了表达的清楚,影片用了每个人不同的身姿、习惯和动作造型,利用每个人讲话时不同的语音语调和咳嗽等,不但使观众看清整个事态的演变,分清每个人物,而且能透过动作窥见人物内心活动。在砖窑那场戏里,王金与犯人们的对立情绪缓和了,双方开始交谈了。在这水井一般的砖窑里,阳光只能从顶部照射进去,创作人员便因势利导,利用窑顶射下来的阳光拍摄。强烈的顶光效果,使人脸在镜头上变形了,甚至难看了。可编导并不回避这种畸变,也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用辅助光冲淡顶光效果,或让光影和造型配合内容中所具有的和解气氛,而是刻意表现视觉造型与内容的对立,故意运用顶光,强调眼窝、面颊、颧骨下的大块阴影,这样形成一种反衬,暗示着他们虽然身陷囹圄,面容丑陋,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心中不乏善良和美好。
其四,这部影片的造型构思,不再是单个画面、单镜头的设想安排,而是注重整个影片造型思维的总体设想,根据全片精神情绪的总的发展,在视像上谋篇布局。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整部影片的色彩显现出蒙太奇结构。影片的前部,以黑色调为主,黑暗的牢房,黑黝肮脏的脸,黑森森的刑场,黑色的主调表达了压抑、沉闷的气氛。影片中部,以红色调为主。在那场突发的遭遇战中,血的洗礼、火的燃烧、红光的爆炸所弥漫、所放射的一点一点、一片一片的红,变成了从黑的压抑走向红的释放的情绪转换。影片的尾部,以白色调为主,这时各种人物走完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历程,找到了各自的归宿,有的人物质生命毁灭了,精神生命却永存了。于是画面上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旷野,明朗灿烂的阳光,辽阔高远的天空。大量的白色调是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象征着升华和新生,全片也走完了由黑到红,由红到白的色彩历程。
其五,这部影片与它之前的中国电影相比,可以说是最具有雕塑感,最富有造型力度的了。为了表现生死存亡中,凝聚血肉,誓死抗敌的民族精神,艺术家们把造型力度作为自己明确的创作追求,他们意识到在所有色彩对比中,黑白对比是最强烈的,所以,他们有意创作出版画般的黑白对比效果。他们还明白,自己所摄录的是一片“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的灾难大地,表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场艰苦斗争,所以任何鲜艳跳跃的色彩都与这一情感意向背道而驰。于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人物服装以黑、白、灰为主,在外景和内景中,避开了所有鲜艳的色彩,在光影安排设计上,内景运用了房屋结构所造成的明暗光区,外景运用强烈阳光造成的亮面和阴影,光线处理中的黑白大反差,强烈地表现了力之美。在摄影机的调度方面,影片不断出现强烈有力的“静态画面”,出现人物雕塑般的造型,例如八个罪犯一张张狰狞、粗野的脸,结尾王金与许志在荒凉大地上顶天屹立的身影,这些线条直硬的静止画面与运动画面相对比而存在,反衬出强烈的力度。
造型的力度还表现在肖像的处理上,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那种不分场合地点,把人物拍得漂漂亮亮、白白嫩嫩的了。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人物脸上粗糙的皮肤,干裂的嘴唇,阴暗牢房里的脏脸,生死搏斗中扭曲的、精瘦的身躯,昏暗光线里破旧的衣衫。这些造型也体现出残酷环境下残酷斗争所迸射出的坚强力度。
《一个和八个》的视觉造型,充分发挥了它的表意、叙事、抒情功能,它的强烈的冲击力,不仅震动了中国影坛,而且揭开了中国当代电影视像造型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