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这是一部非常风格化的作品,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威尔士骑士,他来到一处神秘的古堡,在那里他见到了圣杯的幻像,但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次日清晨,古堡人去楼空,骑士继续出行,当他猛然醒悟到自己看到了圣杯再回去时,古堡已经消失,于是他只能继续他的圣杯寻访之旅。影片完全在摄影棚内拍摄,布景故意做得很“假”,而且台词和动作多有重复,颇有一点曲艺的效果。 初看Perceval le Gaulois,我感到自己是坐在电影院里看舞台剧。一抹深蓝的幕布,几行泛着金属光泽的球形树,地平线处的城堡,和蜿蜒的小径。
Perceval的马穿过树林,达达的马蹄承接着chorus那悠扬的旁白,模糊了电影、戏剧,甚至绘画、文学之间的界限。
我跟70年代法国电影之间的距离,大概就像Eric Rohmer与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距离一样遥远。作为一个现代观众,我对新浪潮电影的理解无力正如现代导演试图还原一幅中世纪图景时的惶惑。当我们试图淌过时光之河去追忆往昔,会发现我们自身已经在这静止的河流里激起波澜。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重现都不免改变历史本身,任何追忆的过程都伴随着回忆自身的变化。
改编自12世纪Chrétien de Troyes的骑士传奇,Perceval的故事在Rohmer的镜头里凝固成一幅画。导演既不再野心勃勃地试图重现一个逝去的时代,也不指望让Chrétien的书在800年后的荧幕上复活。展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非世界本身,我们在后现代文学作品里时时感到这20世纪的遗风。
也许Perceval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叙事方式。暂且不提chorus的出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erceval在念台词之前,总是加上“Perceval说…”,或者“他说…”。演员在表演一个角色的同时,也在叙述他 /她自己的表演。所以演员们既身处其中,也置身事外。这一点倒是照应了Pasolini所说的电影的双重性:我们一方面看到角色所看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看到作为旁观者的导演所看到的角色所处的世界。
我们真的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个时刻吗?当我说“我很快乐”的时候,那个让我快乐的时刻已经逝去了,我只是在叙述那个时刻,因为行为转化成感知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已经离开那个行为所处的时刻了。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
Perceval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它的舞台。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mise-en-scène,简单点说就是镜头的构成,包括舞台背景、人物动作、服饰、道具等等。Perceval中人物那僵硬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那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建筑,以及那些程式化的树与道路,营造出一种中世纪装饰画效果。像在那些久远时代的宫廷壁画中一样,Rohmer创造出来的Perceval是一个平面的像,是一幅被时间冲蚀了很久的褪了色的画。
Perceval是一个关于寻梦的故事,像在许多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传说中一样,年轻的主角只身流浪,从历经沧桑的人那里得到忠告,拜访一位国王,拯救一个陌生的公主,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他出发时只带着一个叫做“骑士”的念头,归来时已然成为不朽的化身;他曾经从别人身上夺来一套骑士的行头,他说:“看啊,这覆着盔甲的身体刀枪不入,似乎它与他已经连为一体,不可分割”,而他终于意识到,骑士之所以成为骑士,不是因为他穿的什么,拿着什么样的武器,战胜了什么人;当一个人成为骑士,他的衣服便成为盔甲,他的剑便成为荣耀本身。
与其说是对古典的重塑,Perceval le Gaulois更像是Rohmer向Chrétien的致敬。
它是一个印象,一页诗,一块时光的碎片。
观看Perceval对于我,如同置身古董店,被旧日的浓浓气息包围着,我凝视着这来自时光之河另一头的世界,深知我永远无法经历那个时代,然而我回忆,也期待。因为这骑士梦也属于我。
Perceval的马穿过树林,达达的马蹄承接着chorus那悠扬的旁白,模糊了电影、戏剧,甚至绘画、文学之间的界限。
我跟70年代法国电影之间的距离,大概就像Eric Rohmer与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距离一样遥远。作为一个现代观众,我对新浪潮电影的理解无力正如现代导演试图还原一幅中世纪图景时的惶惑。当我们试图淌过时光之河去追忆往昔,会发现我们自身已经在这静止的河流里激起波澜。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重现都不免改变历史本身,任何追忆的过程都伴随着回忆自身的变化。
改编自12世纪Chrétien de Troyes的骑士传奇,Perceval的故事在Rohmer的镜头里凝固成一幅画。导演既不再野心勃勃地试图重现一个逝去的时代,也不指望让Chrétien的书在800年后的荧幕上复活。展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非世界本身,我们在后现代文学作品里时时感到这20世纪的遗风。
也许Perceval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叙事方式。暂且不提chorus的出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erceval在念台词之前,总是加上“Perceval说…”,或者“他说…”。演员在表演一个角色的同时,也在叙述他 /她自己的表演。所以演员们既身处其中,也置身事外。这一点倒是照应了Pasolini所说的电影的双重性:我们一方面看到角色所看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看到作为旁观者的导演所看到的角色所处的世界。
我们真的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个时刻吗?当我说“我很快乐”的时候,那个让我快乐的时刻已经逝去了,我只是在叙述那个时刻,因为行为转化成感知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已经离开那个行为所处的时刻了。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
Perceval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它的舞台。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mise-en-scène,简单点说就是镜头的构成,包括舞台背景、人物动作、服饰、道具等等。Perceval中人物那僵硬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那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建筑,以及那些程式化的树与道路,营造出一种中世纪装饰画效果。像在那些久远时代的宫廷壁画中一样,Rohmer创造出来的Perceval是一个平面的像,是一幅被时间冲蚀了很久的褪了色的画。
Perceval是一个关于寻梦的故事,像在许多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传说中一样,年轻的主角只身流浪,从历经沧桑的人那里得到忠告,拜访一位国王,拯救一个陌生的公主,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他出发时只带着一个叫做“骑士”的念头,归来时已然成为不朽的化身;他曾经从别人身上夺来一套骑士的行头,他说:“看啊,这覆着盔甲的身体刀枪不入,似乎它与他已经连为一体,不可分割”,而他终于意识到,骑士之所以成为骑士,不是因为他穿的什么,拿着什么样的武器,战胜了什么人;当一个人成为骑士,他的衣服便成为盔甲,他的剑便成为荣耀本身。
与其说是对古典的重塑,Perceval le Gaulois更像是Rohmer向Chrétien的致敬。
它是一个印象,一页诗,一块时光的碎片。
观看Perceval对于我,如同置身古董店,被旧日的浓浓气息包围着,我凝视着这来自时光之河另一头的世界,深知我永远无法经历那个时代,然而我回忆,也期待。因为这骑士梦也属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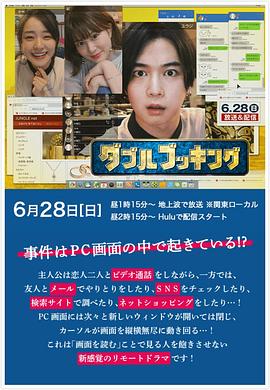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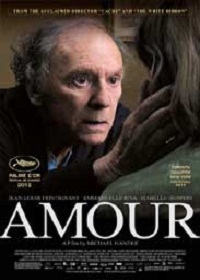




帕西法尔影评
Perceval的马穿过树林,达达的马蹄承接着chorus那悠扬的旁白,模糊了电影、戏剧,甚至绘画、文学之间的界限。
我跟70年代法国电影之间的距离,大概就像Eric Rohmer与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距离一样遥远。作为一个现代观众,我对新浪潮电影的理解无力正如现代导演试图还原一幅中世纪图景时的惶惑。当我们试图淌过时光之河去追忆往昔,会发现我们自身已经在这静止的河流里激起波澜。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重现都不免改变历史本身,任何追忆的过程都伴随着回忆自身的变化。
改编自12世纪Chrétien de Troyes的骑士传奇,Perceval的故事在Rohmer的镜头里凝固成一幅画。导演既不再野心勃勃地试图重现一个逝去的时代,也不指望让Chrétien的书在800年后的荧幕上复活。展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非世界本身,我们在后现代文学作品里时时感到这20世纪的遗风。
也许Perceval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叙事方式。暂且不提chorus的出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erceval在念台词之前,总是加上“Perceval说…”,或者“他说…”。演员在表演一个角色的同时,也在叙述他 /她自己的表演。所以演员们既身处其中,也置身事外。这一点倒是照应了Pasolini所说的电影的双重性:我们一方面看到角色所看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看到作为旁观者的导演所看到的角色所处的世界。
我们真的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个时刻吗?当我说“我很快乐”的时候,那个让我快乐的时刻已经逝去了,我只是在叙述那个时刻,因为行为转化成感知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已经离开那个行为所处的时刻了。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
Perceval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它的舞台。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mise-en-scène,简单点说就是镜头的构成,包括舞台背景、人物动作、服饰、道具等等。Perceval中人物那僵硬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那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建筑,以及那些程式化的树与道路,营造出一种中世纪装饰画效果。像在那些久远时代的宫廷壁画中一样,Rohmer创造出来的Perceval是一个平面的像,是一幅被时间冲蚀了很久的褪了色的画。
Perceval是一个关于寻梦的故事,像在许多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传说中一样,年轻的主角只身流浪,从历经沧桑的人那里得到忠告,拜访一位国王,拯救一个陌生的公主,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他出发时只带着一个叫做“骑士”的念头,归来时已然成为不朽的化身;他曾经从别人身上夺来一套骑士的行头,他说:“看啊,这覆着盔甲的身体刀枪不入,似乎它与他已经连为一体,不可分割”,而他终于意识到,骑士之所以成为骑士,不是因为他穿的什么,拿着什么样的武器,战胜了什么人;当一个人成为骑士,他的衣服便成为盔甲,他的剑便成为荣耀本身。
与其说是对古典的重塑,Perceval le Gaulois更像是Rohmer向Chrétien的致敬。
它是一个印象,一页诗,一块时光的碎片。
观看Perceval对于我,如同置身古董店,被旧日的浓浓气息包围着,我凝视着这来自时光之河另一头的世界,深知我永远无法经历那个时代,然而我回忆,也期待。因为这骑士梦也属于我。